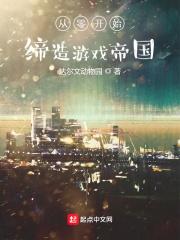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大唐:天上掉下个铜板都得姓李 > 第1548章 太纠结(第3页)
第1548章 太纠结(第3页)
也不能靠着与太上皇的情谊,在官场上混一辈子。
所以,在新旧交替之际,自己在利州兢兢业业的做事,战战兢兢的回长安,见过陛下之后,总算是将心放回了肚子里。
武士彠看向杨夫人。
“如此一说,你可明白我为何犹豫了?”武士彠苦笑:“泾阳王明面上倒是没什么,实际上暗地里早就已经处于漩涡中心了,咱们贸然凑上去。。。。。。”
杨夫人微微摇头。
她倒是觉得,自家夫君的担忧,是多虑的。
"夫君。"她抬眸时,眼底竟闪着奇异的光亮,"正因为如此,咱们才更该去。"
武士彠愕然。
“泾阳王的确是因为佛寺的缘故,得罪了不少人,可是,他得罪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反过来想想,他在长安,就没有交好的人吗?他所交好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这两人,我倒也留意了,与泾阳王府之间相互送年礼的人家。”
那都是跟在陛下身边的重臣,都是陛下的左膀右臂。”
“说白了,他们是一起的。”
“如今,明面上暗地里,都在角力,新旧交替的,不仅仅是一个年号,还有年号底下的人。”
“不管怎么样,都是要选择,要站边的。”
“想着两边都不沾?还能在圈子里如鱼得水?哪里会有这样的好事?”
杨夫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书院里只有媚儿一个出身国公家的孩子吗?”
“那程家,尉迟家,这两家的小子,不也在书院吗?”
“等到来年夏天,书院要考试的时候,指不定还会有哪些勋贵官员,会让自家孩子去考呢。”
"媚儿若能在书院立足,将来便是武家在长安的耳目。"杨夫人声音轻得像羽毛,却字字千钧:“武家商贾出身,朝中无人,总要更费心经营才行。”
杨夫人绝对不会让武士彠的想法影响女儿去书院读书的事。
眼下如何,都能应对,毕竟太上皇还在,陛下更是正当壮年,至于将来太子如何,那是将来的事情。
而让女儿去书院读书,为的就是她们母女的将来。
武士彠听过这些话后,心中也是摇摆不定。
因为,说的也对。
“媚儿是咱们最聪慧的孩子,送去书院读书,不指望将来她能有多好的前程,她也不可能像男儿一样在朝堂上有多少建树。”
“总要有个名头,将来家里的孩子,与旁人家结亲,也能挑上一挑。”杨夫人说道:“不止是咱们家的女儿们,男儿也要娶亲呢。”
武士彠颔。
“说的也对。”
闭上眼睛思索一会儿。
“罢了。”武士彠长叹一声,从袖中取出私印盖在了礼单上。
“明日,我亲自去。”
听到武士彠应下,杨夫人这才放下心来。
而话落在武士彠的两个儿子身上,这才让武士彠应下这件事,如此,杨夫人心里的疙瘩,也是过不去了。
看着眼前的武士彠,杨夫人默默行礼后,离开了书房。
站在廊下,看着空中飘落的零零散散的小雪花,嘴中呼出白雾。
从什么时候,自己开始变得这么能算计了。。。。。
曾经的自己,笃信佛教,自在闺房之中的时候,便是想着往后青灯古佛。
结果却是因为太上皇的一道旨意,下嫁给了武士彠。
所谓“新旧”之争,从一开始,就落在了自己的身上。
自己是“旧”,武士彠是“新”。
新旧之间无法融洽,姻亲关系,就成了平衡的手段。
弘农杨氏,宗室之女。
卖木头的娶了士族女,大家可以做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