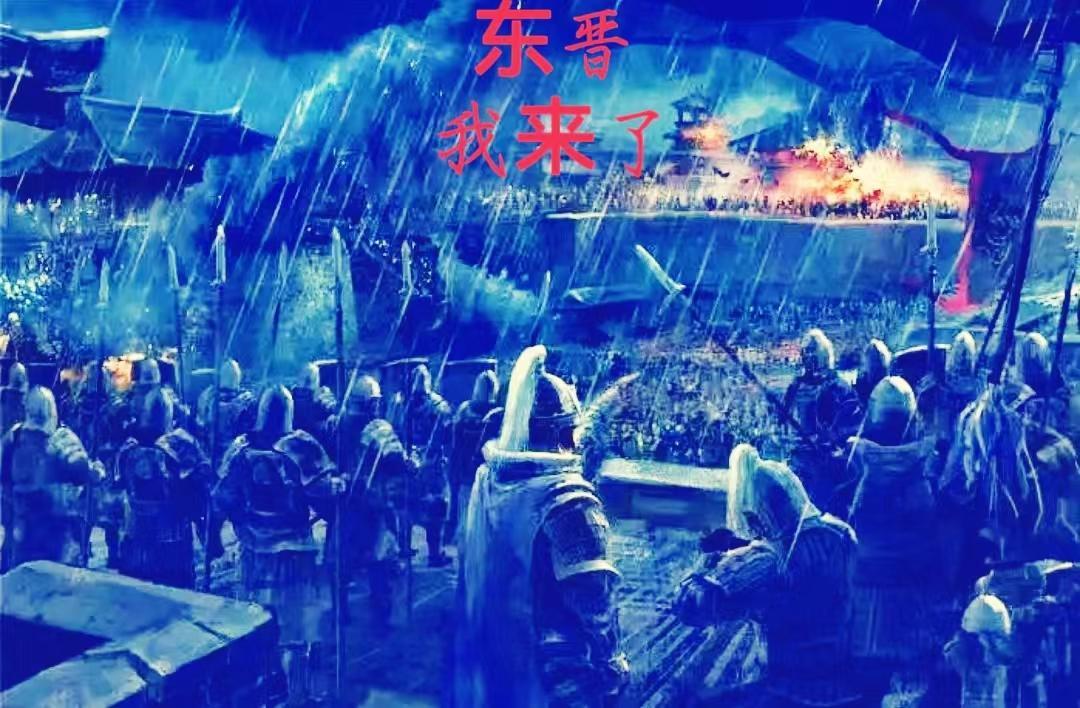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女尊:陨落后,他们求我别摆烂 > 冷月翎 现代视角5(第2页)
冷月翎 现代视角5(第2页)
我知道,他在看,在看我这颗冷家留下的种子,究竟能出怎样的芽。
第一步,是梳理。
我几乎不眠不休,靠着对冷家商业版图的模糊记忆、母亲偶尔提及的零星信息,以及徐伯提供的线索,开始疯狂地梳理、比对、追踪。
冷家的核心产业已被瓜分殆尽,但那些边缘的、不起眼的、甚至是以他人名义代持的资产,还在。
瑞士银行里,母亲以我名义开设的信托基金,因为设定在我成年后才生效,侥幸逃过一劫。
爷爷早年以“礼物”形式赠与我的一些公司干股,虽然占比小,但关键时刻也能汇聚成流。
甚至,冷家老宅地下保险库里,还有一批未被现的、价值连城的古董金条——这是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抱着我当故事说给我听的“藏宝游戏”,我至今记得他当时狡黠的眼神和那句“给小月翎留的小金库”。
第二步,是收回。
这过程远比梳理艰难血腥。
那些嗅到血腥味的鬣狗,怎么可能轻易吐出到嘴的肉?!
我动用了一切能动用的手段。
法律诉讼、股权争夺、甚至是一些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威逼利诱。
徐伯派来的人很好用,他们沉默、高效,总能“恰到好处”地出现在谈判对手的家门口,或者“无意间”透露一些对方极力想掩盖的秘密。
“李总,您挪用公司公款在海外给情人买别墅的证据,想必尊夫人会很感兴趣。”
“张董,您儿子在美国肇事逃逸的事情,好像还没处理干净?”
“王经理,吃掉冷家那家子公司很爽吧?但账目做得太糙了,你说,我要是把这些漏洞捅给税务局,会怎么样?”
……
我的声音通过变声器处理,冰冷而没有起伏。
电话那头的人,往往从最初的嚣张,到惊疑,再到最后的恐惧妥协。
非常时期,行非常手段。
道德,那是活着的人才有资格讲的东西。
第三步,是整合与稳定。
收回的散碎资产需要快整合,形成合力。
我以那些未被冻结的海外账户和信托基金为基点,注册了数家新的空壳公司,交叉持股,层层嵌套,形成一个复杂而隐秘的网络。
收回的资产被迅注入这些公司。
同时,我瞄准了冷氏集团崩盘后跌入谷底的股价。
市场上充斥着恐慌性抛售。
我调动所有能调动的资金,通过那些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空壳公司,悄无声息地、分批分量地吸纳市面上的流通股。
这就像一场豪赌。
赌冷家这块招牌还有残余的价值,赌市场的恐慌终会过去。
我甚至匿名释放出一些“冷家尚有隐秘资产未被现”、“多方神秘资本正在悄悄吸纳冷氏股份”的利好消息,配合我的吸筹动作,慢慢稳住下跌的势头。
这个过程极其耗费心神,资金链数次濒临断裂。
我几乎住在了那间临时的“作战室”,眼睛里布满血丝,咖啡当水喝。
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和k线图,就是我世界的全部。
有一次,我因为连续熬夜和高强度计算,眼前一黑差点晕倒。
是徐伯及时扶住了我,沉默地递上一杯参茶。“小姐,老爷子问,是否需要……”
“不需要。”我打断他,撑着桌子站稳,目光重新聚焦到屏幕上,“告诉他,我能搞定。”
我不知道外祖父听到这句话时是什么表情。
但我必须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