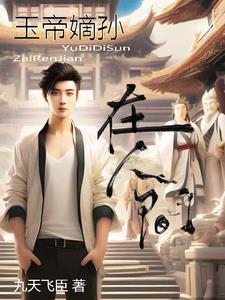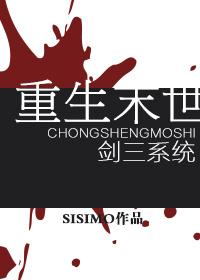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九转金丹炉第2部 > 第559章 3日子熬药人心成丹 一本册子的万里漂流(第2页)
第559章 3日子熬药人心成丹 一本册子的万里漂流(第2页)
暮色渐浓,客栈的灯笼亮了起来,映着窗纸上三人一狐的影子,温馨得像幅画。孟明远把新记的条目仔细描了描,忽然觉得,这《百姓方》上的每个字,都沾着人间的烟火,带着草木的呼吸,而他们的旅程,不过是跟着这份呼吸,慢慢走向更热闹、更踏实的人间罢了。
马车进入中原腹地,官道渐宽,往来商旅也多了起来。路边的驿站旁,常有行脚僧歇脚,青灰色的僧袍在风尘里格外醒目。这日歇在一家客栈,隔壁桌的僧人正对着一碗汤药愁,眉头皱得像团拧干的布。
“小师父这药怎么了?”林恩灿忍不住问。
僧人苦笑:“这‘黄连’太苦,每次喝都像吞火炭,实在难以下咽。”
林恩灿看了看他的药碗,里面的汤药黄澄澄的,确实透着股冲鼻的苦气:“黄连虽苦,却能清心火。小师父若是觉得难喝,不妨试试加两颗蜜枣同煮,既能中和苦味,又不影响药效。”
僧人将信将疑,让客栈后厨煮了碗加蜜枣的黄连汤,果然苦中带甜,顺口多了。他合十行礼:“多谢先生指点。出家人慈悲,若能让病患不觉药苦,也是功德一件。”
孟明远在本子上记下:“黄连配蜜枣,减苦增效,中原僧人传。”写完忽然笑道:“先生,您这法子倒像变戏法,再苦的药经您一调,就有了暖意。”
“药是治病的,不是罚人的。”林恩灿望着窗外往来的车马,“就像这中原大地,既能种得下苦黄连,也长得出甜枣子,刚柔相济,才是日子的本味。”
往前行了几日,到了一座古镇,镇上有座百年药坊,门楣上“济世堂”三个字被岁月磨得亮。药坊掌柜是个瘸腿的老者,见林恩灿背着药箱,便邀进去喝茶。
“先生看着面生,是游方的医者?”老者呷了口茶,“我这药坊开了三代,见过不少医者,像先生这样带着本子记方子的,倒是少见。”
林恩灿取出《百姓方》:“不过是觉得民间智慧可贵,想留些念想。比如这中原的‘地骨皮’,我听说用来煮水治消渴症,比一味用知母更稳妥?”
老者眼睛一亮:“正是!我祖父传下的法子,地骨皮配桑白皮,再加些粳米,煮成粥喝,既能降糖,又不伤脾胃。好多富贵人家得了消渴,都是靠这方子稳住的。”
孟明远赶紧记录,老者又指着墙上的药谱:“你看这‘冬葵子’,年轻人嫌它普通,却不知用它煮水通乳,比那些名贵药材管用多了。去年镇上张屠户的婆娘生娃后没奶水,就是靠这草籽救了急。”
林恩灿听得认真,忽然道:“老掌柜,我这《百姓方》想借您药坊的地方誊抄一份,若是有人需要,便可自行取阅。”
老者抚着胡须笑:“好主意!我这药坊正好缺本实用的土方集,先生若不嫌弃,我让学徒帮着抄,管够笔墨!”
接下来的几日,药坊里多了几张方桌,学徒们围着《百姓方》誊抄,墨香混着药香,竟有种特别的安宁。林恩灿则在一旁解答疑问,偶尔添些新的注解——比如“地骨皮要取枸杞根的内皮,外层粗皮需刮去”,“冬葵子需微炒,否则易致腹泻”。
孟明远看着一张张抄好的方子,忽然道:“先生,您看这些纸页,多像一片片叶子,要把草木的故事带到更远的地方。”
林恩灿望着窗外掠过的流云,笑了:“不止是草木的故事,还有人的。你看那抄方的学徒,将来会把这些法子教给徒弟;来取方的百姓,会把方子传给邻里。这才是真正的传承——像中原的黄河水,汇了千条溪,才成了奔涌的河。”
离开古镇时,老者送了他们一捆“牛膝”,说是中原特产的“怀牛膝”,补肝肾比普通牛膝更胜一筹。“先生带着,路上若遇着腰腿不便的,能派上用场。”
马车驶离镇子,孟明远把怀牛膝小心地收好,忽然现灵狐的窝里多了片冬葵子的叶子,想来是药坊的学徒偷偷放的。他笑着指给林恩灿看,林恩灿望着那片叶子,忽然觉得,这一路的草木与人,早已在他心里扎了根,了芽,长成了一片遮风挡雨的林。
而前路,还有更多的种子等着被播撒,更多的绿意等着被见证。这修行的路,便在这一程程的遇见里,慢慢铺成了人间的模样。
马车过了黄河,风里就带了些北方的燥意。路边的白杨树叶子落得簌簌响,像在数着日子往深里走。孟明远正对着《百姓方》上“秋燥咳嗽方”琢磨,忽然听见车外传来一阵急促的咳嗽声。
掀帘一看,是个挑着货担的老汉,咳得腰都弯成了弓,额头上渗着冷汗。林恩灿赶紧让车夫停车,跳下去扶住老汉:“大爷,您这是燥着了吧?”
老汉喘着气点头:“入秋就犯这毛病,咳得夜里睡不着……”
林恩灿从药箱里翻出晒干的桑白皮和杏仁,又让孟明远取来路边的野菊花:“这三样煮水喝,桑白皮清肺,杏仁润喉,野菊花败火,比抓药方便多了。”他边说边帮老汉把货担挪到树荫下,“您先歇着,我去前边村里借口锅,煮好给您送来。”
等水开的功夫,老汉指着货担里的红枣笑:“这是自家树上结的,甜着呢。先生要是不嫌弃,带些路上吃。”孟明远接过来,见红枣个个饱满,在衣襟上擦了擦就塞给林恩灿一颗:“您尝尝,比药甜。”
水沸了,药香混着枣香飘出来。老汉喝了两碗,果然咳嗽轻了些,挑起担子时脚步都稳了:“先生这方子,比镇上大夫开的药还灵!”他非要往林恩灿手里塞一把红枣,“记着啊,过了这村,北边的枣就没这么甜了。”
马车重新上路时,孟明远把红枣往《百姓方》里夹了一颗,笑道:“这下连方子都带着枣香了。”林恩灿看着那抹红,忽然觉得这册子更沉了些——每一页都裹着人的热气,比墨迹更鲜亮。
前方的路隐在黄栌林里,叶子正红得像燃着的火。灵狐从车座下钻出来,嘴里叼着片刚落的红叶,轻轻放在那页“秋燥方”上。林恩灿摸着红叶边缘的锯齿,忽然明白,所谓传承,从来不是纸页上的字,而是这些带着体温的相遇,像落叶归土,又生根芽。
过了黄栌林,风里就掺了些雪粒子。孟明远裹紧了棉袄,看着窗外渐渐变白的田野,忽然指着远处的炊烟喊:“先生您看,那村里准有人家熬着热汤呢!”
林恩灿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一间土坯房的烟囱正冒着笔直的烟,门口堆着半人高的柴火,像是在等赶路的人。马车刚停稳,就有个扎围裙的妇人迎出来,手里还端着个冒热气的粗瓷碗:“听动静就知道是远来的客人,快进屋暖和暖和,刚熬的萝卜汤,驱驱寒!”
屋里的土炕烧得滚烫,妇人把汤碗往炕桌中间一放,萝卜的甜混着肉香直往鼻子里钻。林恩灿喝了两口,忽然指着碗里的生姜片笑:“这法子跟《百姓方》里的‘散寒方’对上了——萝卜顺气,生姜驱寒,再加把胡椒,比单喝姜汤更润胃。”
妇人拍着大腿乐:“还是先生懂行!这是我当家的琢磨出来的,他跑大车走南闯北,说这么喝着舒坦,比抓药省钱还管用。”正说着,门外闯进来个裹着虎头帽的娃,手里举着串冻红的山楂,非要塞给林恩灿:“爷爷说,客人要吃甜的才不冷。”
孟明远赶紧掏出本子记:“萝卜生姜胡椒汤,驱寒顺气,北方农妇传。”写完又把山楂串往林恩灿手里塞,“您看,连娃都知道添方子呢。”
雪下大了,妇人非要留他们住下,说炕梢还能挤两个人。夜里听着窗外的雪落声,林恩灿摸着怀里温热的《百姓方》,纸页上的字仿佛都活了过来——每个方子背后,都站着一个笑着递汤的妇人,一个举着山楂的娃,还有无数个把日子过成药方的普通人。
第二天推开门,雪没到了膝盖。妇人的丈夫套上牛车送他们,车轮碾过积雪出咯吱声,像在为新添的方子伴奏。孟明远忽然哼起了小调,调子是村里老人教的,词儿却换成了他们一路记的方子,林恩灿听着,忽然觉得这趟路啊,走得比任何修行都实在。
牛车在雪地里行了半日,终于到了官道。告别了送他们的农夫,马车重新上了路。雪光晃眼,林恩灿掀帘时,忽见道旁的枯草堆里,有个蜷缩的身影。
“停车!”他话音未落,人已跳下车。那是个衣衫褴褛的少年,怀里紧紧抱着个破布包,冻得嘴唇紫,气息微弱。林恩灿摸了摸他的额头,滚烫得吓人。
“是风寒入体,烧得厉害。”林恩灿解开自己的外袍,裹在少年身上,又让孟明远取来姜茶和随身携带的“风寒散”——这是用麻黄、桂枝等药磨成的粉,用热酒冲服最见效。
少年被灌了半杯姜茶,又喂了药粉,脸色渐渐缓过来些,睁着蒙眬的眼问:“我……我的药……”
他怀里的破布包滚落在雪地里,露出里面半包干枯的“防风”。孟明远捡起来,见草根上还沾着泥土:“这是你采的?”
少年点点头,声音颤:“俺娘咳得厉害,郎中说防风能治……俺去山里采,迷了路……”
林恩灿心头一软,摸了摸他的头:“别怕,你娘的病,我帮你治。”他让车夫调转车头,“先去你家看看。”
少年的家在山坳里,一间破土房,四壁漏风。炕上躺着个妇人,咳嗽声像破锣,见儿子被人送回来,挣扎着想坐起,却动不了身。林恩灿搭脉后,眉头微蹙:“是风寒郁肺,得用麻黄汤加减,但她身子虚,得先补补元气。”
他从药箱里取出怀牛膝和当归,又让少年去院里挖了些“地环”——这是北方常见的野菜,有润肺的功效。“牛膝当归炖鸡汤,地环炒着吃,先把身子补起来,再用药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