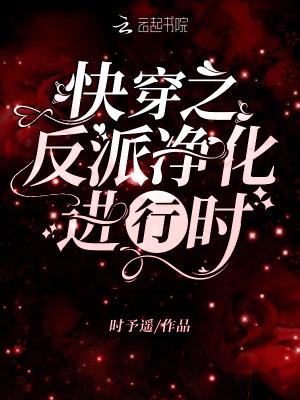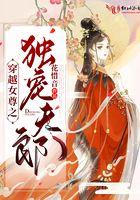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很平凡的一生吧? > 第727章 大同府改革(第1页)
第727章 大同府改革(第1页)
暮色漫过东城的青砖灰瓦时,李星群正对着沙盘上西南坊的位置轻叩指尖。田维刚从篱笆外探查回来,靴底还沾着新鲜的泥土:“大人,张茂又加派了二十个守卫,听说坊里的铁匠铺都在连夜打刀。”
“随他去。”李星群推开窗,晚风卷着新翻的泥土味涌进来,“一群跳梁小丑聚在一处,总好过散在城里作乱。”他转身指向案上的文卷,“把精力都放在新政上,西南坊的事,几年后再说。”
三日后的府衙大堂,十二盏羊角灯将梁柱照得亮如白昼。韩严法捧着新铸的铜印,印面上“大同府法院”五个篆字泛着冷光;田维腰间的佩刀换了制式,刀鞘上錾着“公安”二字;苏铁冠正与李助核对账册,算盘珠子打得噼啪作响。
“韩院长,”李星群将一卷《刑狱规范》推过去,“凡民告官、邻里纠纷,皆由法院受理,刑曹不得插手。记住,法字当前,不分贵贱。”韩严法刚正的脸上难得露出郑重,将文书卷好塞进袖中。
田维摸着新刀鞘直咧嘴:“大人,这公安局要管偷鸡摸狗,还要巡街抓贼?”
“不止。”李星群在沙盘上圈出十二处街巷,“设十二个巡捕房,白日维持市集秩序,夜里查禁宵禁。尤其要盯着粮行与银号,不许再像张茂那样哄抬物价。”他忽然笑了,“你那身刑曹本事,总算有地方施展了。”
苏铁冠这时推了推算盘:“大人,税务局的章程拟好了。商税分三等,绸缎庄抽三成,粮铺抽一成五,走街串巷的货郎免征——”
“改。”李星群打断他,“货郎月入过两贯的,抽半成。穷人生计要保,但也得让他们知道,商税取之于民,最后会变成东城的石板路、西城的水井。”李助在旁补充:“属下已让人刻了税碑,立在市集入口,每笔税银的去向都写得明明白白。”
官场改革的墨迹未干,李星群已带着匠人奔赴城西。昔日萧骨的马场被推平,露出底下黑黢黢的煤层。他踩着煤块对苏铁冠道:“虽然我们学习广东的经验,但是广东是靠海行船,咱们靠煤走车。把这些黑石头炼成焦炭,能让铁器更韧,马车跑得更快。”
为打通陆路贸易,李星群下了三道硬令:其一,征调民夫将大同至代州、应州的土路拓宽至三丈,路面铺以碎石与夯土,遇河架木桥,逢山凿栈道,每十里设一驿站,备有替换的骡马与修补车胎的铁匠;其二,成立“通衢护卫营”,由田维从公安系统抽调百余名精壮,佩长刀护商队,凡持有大同府签“路引”的商队,沿途遇匪可凭文书向驿站求助,护卫营需三日内追讨货物;其三,在通衢市设“度量衡署”,用青铜浇铸标准秤砣、斗斛,刻上官方印记,商户需按月校验量具,作弊者罚银五十两。
西域胡商第一次带着驼队踏入通衢市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直捋胡须:北市的皮毛行前,伙计正用标准秤称着狐裘,旁边立着石碑,刻着“一两一钱皆足”;南市的粮铺里,掌柜用官制斗斛量米,买主可随时到署衙复称。更让他们惊喜的是,驿站不仅提供免费饮水,还能寄存货物,只需付半成保管费——这比在河西走廊被乱收费省下太多。
“这黑石头竟能比木炭耐烧三倍?”胡商头领捏着焦块反复查看时,李星群正让人演示焦炭冶铁:通红的铁水灌入模具,冷却后敲去泥壳,竟是匹铁制马掌,边缘光滑得能照见人影。“用这马掌钉在驼蹄上,单程能多走两百里。”李星群指着账册,“十车焦炭换一车玉石,你我各得其所。”胡商当即拍板,临走时特意多留了两个会说汉话的随从,说是要学这“公平买卖的法子”。
三个月后,西城冒出五座青砖作坊:炼焦厂的烟囱日日喷着灰烟,纺织厂的木机声能传到街尾,罐头厂里,工匠们正将猪肉切块,装入陶罐后用蜡密封,再放到沸水锅里煮半个时辰——这是李星群根据前世记忆改良的法子,虽不及后世罐头耐久,却能让肉类保存两月不坏。
改革的真正难题,藏在寻常百姓的土坯房里。当第一批“大同府学堂”的木牌挂上校门时,李星群正站在王屠户家的院墙外,听着里面的争吵声。
“丫头片子读什么书?能杀猪还是能耕地?”王屠户的粗嗓门震得瓦片颤。李星群推门而入时,见个梳着双丫髻的小姑娘正攥着木棍在地上写字,字迹歪歪扭扭却是“王小花”三个字。
“王屠户,”李星群弯腰捡起小姑娘的木棍,“知道西城的纺织厂吗?那里的织机娘,识得字的每月多领五百钱。”他往墙上一指,那里贴着官府的告示:“女子入学满六年,可优先入厂当学徒,管吃管住月钱一贯。”
王屠户挠着头嘟囔:“可……可她是个丫头……”
“明年我要开罐头厂,装你们家的猪肉。”李星群拍着他的肩膀,力道让屠夫踉跄了半步,“记账、算工钱都要识字的人,你家小花若是读好书,这账房先生的位置,我先给你留着。”小姑娘突然抬头:“我能学算术吗?我想帮爹算卖猪的钱。”
这样的劝说,李星群在三年里重复了两千三百多次。有次在深山里的猎户家,对方举着弓箭不让进门,他踩着屋檐翻进去,蹲在火塘边讲了半夜——从城里学堂的热炕头,讲到纺织厂的女工如何用赚来的钱给家里买耕牛。天快亮时,猎户终于把藏在床底的女儿拽了出来,红着眼眶说:“她娘死得早,我怕她被人欺负……”
三年后的开学典礼,李星群站在新落成的学堂前,看着操场上整齐列队的孩子。王小花已长成半大姑娘,正领着女学生们朗读《大同律》;角落里,那个曾从张茂篱笆下溜出来的少年,胸前别着“全校第一”的木牌。韩严法捧着新刻的律书走过,笑着摇头:“大人,这三年您脚不沾地地跑遍了辖区各庄,眼下学堂刚上正轨,也该松口气了。”
李星群望着远处冒烟的作坊,忽然想起刚到大同的那个午后。那时的广场还飘着血腥味,而此刻,学堂的钟声正穿过市集,惊起一群白鸽。他摸了摸腰间的马鞭,皮革上的防滑纹已被磨得光滑——这三年跑断腿般的奔波,终究是没白废。
秋意漫过雁门关时,大同府的城门楼外已排起三里长的队伍。五台县百姓背着捆成卷的被褥,怀里揣着李星群当年签的地契——那纸张边角早已磨烂,却被攥得温热。守城的士兵每验过一张,就在名册上画个圈,到日暮时分,朱砂痕迹已密密麻麻爬满了七张纸。
“大人,这是今日的第七百三十三人。”李助将名册递进来时,袖口沾着墨汁,“城西的临时窝棚快搭满了,户曹的算盘珠子都快磨平了。”
李星群望着窗外飘飞的榆叶,指尖在案上敲出轻响。三年前他离任五台县时,曾给百姓留过话:“若遇难处,可往大同寻我。”没成想那老夫子知县竟把个十万人大县折腾得粮价飞涨,商户倒闭,到头来还是要他来接这烂摊子。
“粮仓还能撑多久?”
“顶多半月。”李助压低声音,“城外那百顷地都租给商户种马铃薯了,租金早填进学堂的开销里。现在别说添新校舍,就连灶房的米缸都快见底。”
正说着,柳珏掀帘而入,带来股账房特有的油墨味。她将一本厚厚的账册拍在案上:“五台县来的青壮有两千三百多,正好派上用场。城西的煤矿不是缺人手吗?让他们去挖煤,管吃管住,月钱给两贯。”
李星群眉头猛地一皱:“挖煤?你没见矿上那些老矿工,十年下来个个咳嗽得直不起腰?那活儿伤根本,不能让他们去遭这份罪。”
“遭罪?”柳珏挑眉,伸手从账册里抽出张纸条,“这是昨日刚登记的农户,一家五口挤在破庙里,小儿子都快冻得不出声了。比起饿死冻死,挖煤算什么遭罪?”她走到窗前,望着窝棚区升起的袅袅炊烟,“夫君别忘了,庄子与惠子论大葫芦,有用无用,本就看怎么放。五台县人多是负担,但若用好了,就是撬动大同府的支杆。”
李星群指尖停在案上,想起前世课本里那些矿工矽肺的照片,喉间有些紧:“可……”
“可你总把五台县人当自家人,想格外照顾?”柳珏转过身,鬓边的珠花随着动作轻晃,“当年你在五台县教他们种番薯,现在却要因‘照顾’二字困住手脚?夫君可知,通衢市的铁匠铺里,三个大同本地工匠已经在抱怨活儿少了——人多了才有竞争,有竞争才知上进,这难道不是你办学堂想教给孩子们的道理?”
“我不是这个意思……”李星群的声音弱了下去。他确实对五台县百姓有份特殊的牵挂,那些人曾跟着他在田埂上摸爬滚打,看着他从一个青涩的知县长成能独当一面的知府。
柳珏忽然叹了口气,伸手按住他的手背:“我知道你心疼他们。但你是大同府知府,手里握着的是全城人的生计。若为了偏私坏了规矩,日后怎么服众?”她翻开账册,指着其中一页,“你看,这些人里有会烧陶的,有能打铁的,还有几个识得些字的。按学堂的考核标准分等派活,既能人尽其用,又能让他们服气,岂不是两全?”
李星群沉默半晌,终于在账册上圈了个红圈:“就按你说的办。但煤矿必须加两条规矩:每日下井不得过四个时辰,每月强制歇工三日,矿上得请大夫常驻。”
消息传开时,窝棚区里炸开了锅。当田维带着吏员宣读考核章程——识三百字以上者可入纺织厂、炼焦厂,能算清百以内加减法者可去修铁路,其余则分配至煤矿或建筑工地——竟有大半人摩拳擦掌。
“修铁路给三贯月钱?”个瘸腿汉子拽着吏员的袖子,“我年轻时在五台县修过栈道,这活儿我能干!”旁边个穿补丁长衫的书生赶紧掏出炭笔:“我能背《论语》,算不算识得字?”
最让人惊讶的是煤矿招募处,不到半日就报满了名额。李星群站在矿口查看时,见个老矿工正给新人们分粗布口罩:“这是李大人特批的,说是能挡挡煤尘。”有个五台县来的后生笑着把口罩往脸上一罩:“比在老家啃观音土强百倍!俺哥在炼焦厂,俺在矿上,俩月就能凑够钱租楼房了!”
柳珏说得没错,高工资成了最好的强心针。那些原本对学堂嗤之鼻的大同本地户,见五台县来的娃凭着识字进了工厂,拿的月钱比自家汉子还多,纷纷扛着板凳去学堂报名。王屠户更是提着半扇猪肉找到校长:“给俺家小花补补课!明年说啥也得考进纺织厂!”
三年时间,三条铁轨从大同府延伸出去,蒸汽火车喷着白汽穿过雁门关时,秦地的商队正赶着骡马在站台上卸货。马和握着李星群的手,指节因激动泛白:“大人您是不知道,靠着这条铁路,咱们的瓷器从大同运到长安,比走水路快了二十日!欠的那些银子早还清了,现在秦商谁家不存着大同的焦炭?”
站在通衢市的过街楼上,李星群望着纵横交错的铁轨,忽然想起柳珏那句“天下为公”。城西的煤矿区盖起了一排排青砖房,矿工们下班后能去澡堂泡澡;学堂的钟声里,女孩们的琅琅书声与男孩们的不相上下;就连西南坊的张茂,也偷偷派人来学度量衡——听说他坊里的百姓总往东城跑,再不改良规矩,怕是要成孤家寡人。
灶房的香气顺着风飘过来,伙夫正把刚出炉的面包往竹篮里装。李星群笑着接过一块,外皮酥脆,内里松软。想当年刚到大同,百姓顿顿不离莜面,如今市集上既有陕北的糜子糕,也有江南的糯米团,连西域胡商带来的葡萄酿都成了寻常饮品。
“夫君在想什么?”柳珏递来一杯热茶,水汽氤氲了她的眉眼。
“在想,”李星群望着远处学堂的飞檐,“当年总怕对不住五台县的乡亲,现在才明白,让所有人都能吃上热乎饭、住上结实房,才是真的对得住他们。”
暮色渐浓时,火车的汽笛声穿过街巷,与学堂的晚钟交织在一处。铁轨旁的路灯次第亮起,昏黄的光晕里,归家的百姓提着菜篮说说笑笑,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那是比任何石碑都更鲜活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