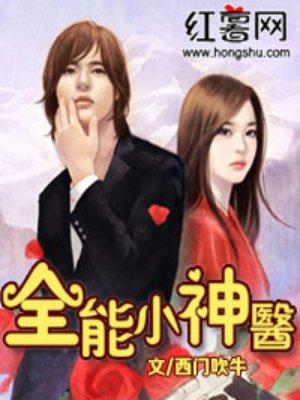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和脱衣舞女郎妈妈一起穿越到异世界 > 第14章 韩月和妇姽以及他们的后来(第4页)
第14章 韩月和妇姽以及他们的后来(第4页)
“死了。”
“怎么死的?”
“病死的。”她说,“听说禅位之后没多久就病了,病了几个月,就死了。”
病死的。
那三个字在那昏黄的亮里飘着,像几片枯树叶。
我望着阿依兰。
望着她那低下去的头,那微微抖的肩膀。
我知道那“病死的”是什么意思。
历史上那些禅位的皇帝,有几个是真正病死的?
我深吸一口气。
那气凉凉的,从喉咙里进去,一直凉到心里。
然后我问。
那问题从嘴里出来,轻轻的。
“阿依兰——那现在的大夏,有多大?”
她抬起头。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望着我。
“很大。”她说,“很大很大。”
“多大?”
她想了想。
那眉头又皱起来,皱得那眉心有两道浅浅的竖纹。
“奴婢也说不太准。”她说,“只知道很大。西边——”
她伸出手。
那手白白的,细细的,在那昏黄的亮里划了一下。
“西边到波斯。”
波斯。
那两个字像两块石头。
波斯。那是伊朗。那是中东。那是离这儿几千里的地方。
“波斯?”我问,“那是哪儿?”
“回主子——”她说,“是西域再往西。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的人长得和我们不一样,信的神也不一样。可那里是大夏的属国,年年要来朝贡的。”
属国。
朝贡。
我脑子里嗡嗡的。
“东边呢?”我问。
“东边到朝鲜。”
朝鲜。
那两个字像两颗小石子。
朝鲜。那是朝鲜半岛。那是东北亚。
“北边呢?”
“北边到北海。”
北海。
那是什么地方?贝加尔湖?还是更北的地方?
“南边呢?”
“南边到海岛。”
海岛。
那是南海?那是东南亚的那些岛屿?
我听着。
听着这些话。
那些话在我脑子里变成一张地图——一张很大的地图,西到波斯,东到朝鲜,北到北海,南到海岛。
那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