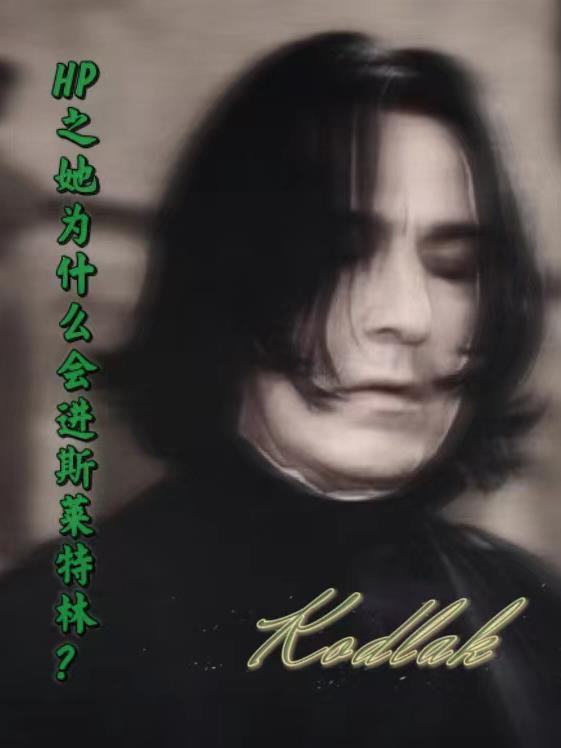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和脱衣舞女郎妈妈一起穿越到异世界 > 第14章 韩月和妇姽以及他们的后来(第21页)
第14章 韩月和妇姽以及他们的后来(第21页)
“那五个孩子呢?都活着吗?”
阿依兰摇摇头。
那摇很慢。
很轻。
“没有。”她说,“只活下来一个。”
只活下来一个。
那六个字像六根针。
“那四个呢?”
“三个夭折了。”阿依兰说,“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一个生下来没几个月就死了,一个一岁多死的,一个三岁多死的。还有一个——”
她停下来。
那脸上的表情很怪。
“还有一个怎么了?”
“还有一个——”阿依兰说,“有很严重的病。”
严重的病。
那四个字像四块石头。
“什么病?”
“不知道。”阿依兰说,“只知道一直病着,躺在床上,不能动,也不能说话。活倒是活着,可跟死了也差不多。”
我听着。
脑子里浮现出一幅画——一个躺在床上的孩子,不会动,不会说话,就那么躺着,躺着,躺了很多年。
“那个孩子多大了?”母亲问。
阿依兰想了想。
“应该——”她说,“三十多了吧。比长公主小一点。”
长公主。
那三个字像三颗小石子。
“长公主?”我问,“谁是长公主?”
阿依兰望着我。
那眼睛大大的,黑黑的,亮亮的。
“就是那个活下来的。”她说,“皇后的第五个孩子。建宁长公主,韩菲雪。”
建宁长公主。
韩菲雪。
那六个字像六颗星星。
“她活下来了?”母亲问。
“嗯。”阿依兰说,“她不仅活下来了,而且——”
她停下来。
那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是羡慕?是惊叹?还是别的什么?
“而且什么?”
“而且——”阿依兰说,“她很健康。身体特别好。从小就不生病,不烧,什么毛病都没有。长得也——”
她又停下来。
“长得怎么了?”
“长得——”阿依兰说,“是天下第一美人。”
天下第一美人。
那六个字像六朵花。
我望着阿依兰。
“天下第一美人?”
“嗯。”阿依兰说,“都这么说。说她长得像天上的仙女,说她一笑,满宫的花都开了,说她的眼睛像星星,说她的皮肤像雪,说她——”
她说不下去了。
只是望着我。
那眼睛里的光很复杂——有向往,有崇拜,有那种“我这辈子都比不上”的光。
我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