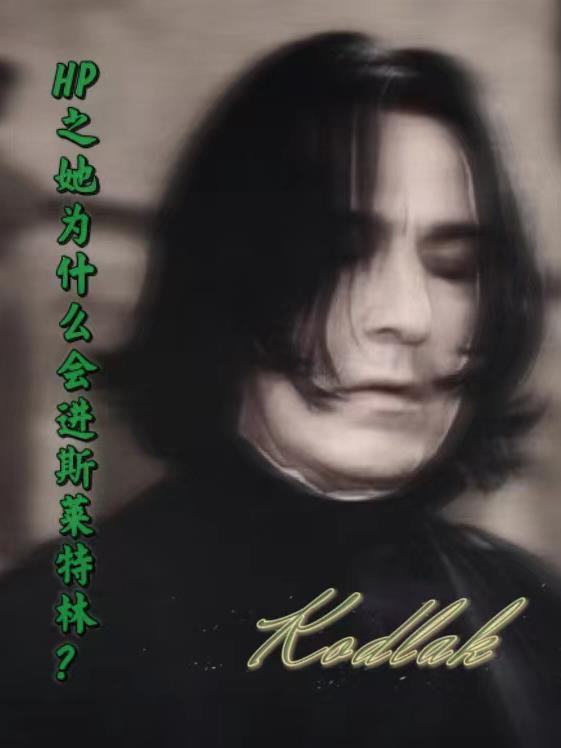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和脱衣舞女郎妈妈一起穿越到异世界 > 第6章 丈夫的职责(第15页)
第6章 丈夫的职责(第15页)
她整个人在我怀里弹起来,胸脯剧烈起伏,那两团饱满的乳肉上下跳动,朱砂痣在晨光里划出一道道暗红色的弧。
她的手指掐进我背上的肉里,掐得生疼。
可她的眼睛在笑。
是真的在笑。
眼角弯下去,嘴角翘起来,整张脸都在那道晨光里亮起来。
她笑着喘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抬起手。
轻轻拍了拍我的脑袋。
“别急。”她的声音还带着喘,却温柔得像在哄小孩,“我们有一整天。”
“一整天?”
“对。”她说,“从今天开始,我什么都不做,就做这一件事。”
“什么事?”
她望着我。
那双眼睛很深,很软,像两潭能溺死人的泉水。
“让你把我灌满。”她说,“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直到这里面——”
她的手从我们紧贴的小腹上滑下去,按在自己小腹上,隔着那层薄薄的皮肉,按在她子宫的位置。
“——住进一个孩子。”
那话像一道闪电,劈进我脑子里。
我望着她。
她也在望着我。
很久。
然后我动了。
不是故意的。
是忍不住。
那东西放在她里面,被那湿润的、柔软的、微微烫的肉壁裹着,裹得它一直在跳,一下一下,像一颗多余的心脏。
每一跳都带着一股冲动,一股想往里钻、往里顶、往最深处冲的冲动。
我顶了一下。
她的眼睛又睁大了一点。
我又顶了一下。
她的嘴张开,又咬住下唇。
我再顶一下。
她整个人往后仰,脖子拉成一道优美的弧线,喉结上下滚动,把那一声冲到嘴边的尖叫又咽回去。
“慢……慢一点……”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像被顶碎的珠子,“太……太深了……”
我慢下来。
可没停。
一下,一下,很慢,很深。
每一下都顶到底,顶到她身体最深处那个最软、最烫、最要命的地方。
她的肉壁裹着我,一收一缩,像无数张嘴在吸,在吮,在把我往更深处拉。
她的手还搂着我的脖子。
她的脸埋在我肩上。
她的身体在我怀里轻轻抖。
那颤抖从她体内传出来,通过那根连接着我们的东西,传到我体内。
我能感觉到她每一次收缩,每一次痉挛,每一次被顶到最深处时那种无法控制的颤抖。
“舒服吗?”
我问。
她把脸埋在我肩上,点了点头。
点得很用力。
“你呢?”她的声音闷闷的,从肩窝里传出来,“舒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