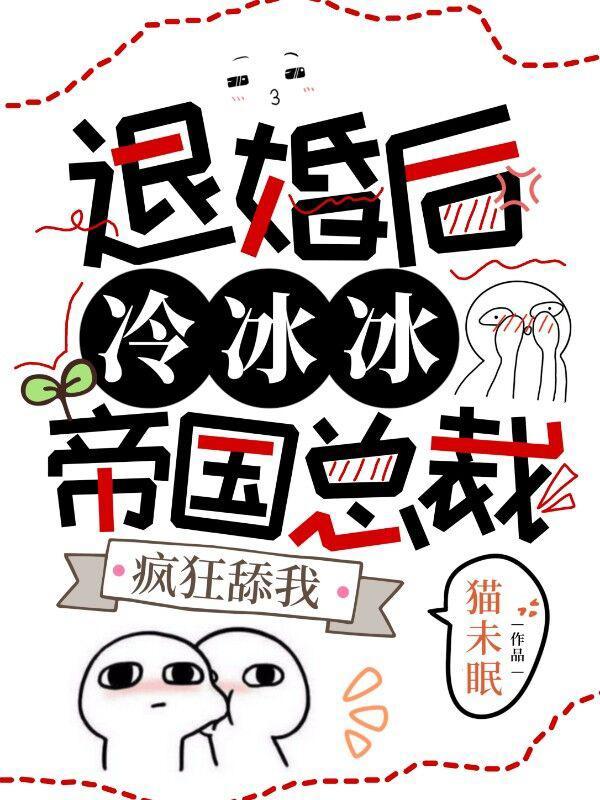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大明崇祯剧本,我偏要万国来朝! > 第658章 舆图指点江山定降表裁成富贵留(第2页)
第658章 舆图指点江山定降表裁成富贵留(第2页)
朱由检重新走回丹陛,每一步都像踩在郑椿的心跳上。
他坐回龙椅,那股睥睨天下的帝王之气,充斥了整座大殿。
“毕爱卿。”
毕自严心中一叹,出列跪倒:“臣在。”
“你算的是户部的小账,朕算的,是天下的大账。”
朱由检的声音沉重如山。
“今日若贪图一时安逸,许了郑氏羁縻,那便是向天下藩属宣告:只要你够狠,只要你会装可怜,哪怕是弑君篡位,大明也可以既往不咎!”
“此例一开,宗藩体系还要不要了?”
“天朝的脸面,还要不要了?”
“到那时,朝鲜效仿,琉球效仿,西南土司人人效仿!届时平叛所耗费的银子,怕是你今日省下的十倍、百倍!”
毕自严如遭雷击,冷汗涔涔而下。
他只想着国库的存银,却忘了这政治上的推倒,会引何等可怕的灾难。
“臣……臣愚钝!臣知罪!”
朱由检那番关于“恶犬”与“王化”的宏论。
瘫软在地的郑椿,最后那点侥幸,被击成了齑粉。
他知道,郑氏完了。
安南所谓的“独立”,在今日之后,也将成为史书中几行淡漠的墨迹。
朱由检俯视着这个被彻底抽掉骨头的安南使臣,眼神里的锋芒缓缓敛去,沉淀为一种深不见底的平静。
“不过……”
帝王的话锋,轻飘飘地一转。
一下就吊起了郑椿那颗正在沉向深渊的心。
朱由检缓缓坐回龙椅。
“上天有好生之德,朕非嗜杀之君。”
“郑氏虽有大逆,但念在你今日尚有几分悔意,且安南百姓无辜。”
“朕,可以给郑氏一条活路。”
郑椿猛地抬头!
他眼中迸出的光彩,是濒死者看到天光的狂喜。
“礼部尚书周延儒。”
朱由检抬手,指向队列中的周延儒。
“这件事,朕交给你去办。”
周延儒心领神会,立刻出列躬身。
“臣,遵旨。”
朱由检的目光再次落在郑椿身上。
“郑椿,你即刻随周尚书下去。”
“该怎么写那份请罪的降表,该如何向安南国内传信,怎么让你家主公郑梉自缚来降……”
“你要好好学,用心学。”
说到此处,朱由检的身子微微前倾。
“若是这降表写得好,写得朕满意了,朕可许你郑氏,如那南边的阮氏一般,留一地富贵。”
“甚至……朕还可以许你郑氏子孙,入我大明朝中,谋个一官半职,永享天朝恩荣。”
“但若写得不好……”
朱由检没有再说下去。
他只是抬起手,轻轻掸了掸龙袍上并不存在的灰尘。
这个动作,却比任何威胁都更具分量。
郑椿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
阮氏归降后的待遇,他一清二楚!虽没了裂土封疆的权力,却也是货真价实的富家翁,背靠大明这棵参天大树,比满门抄斩强过万倍!
“罪臣……罪臣明白!”
“罪臣定当竭心尽力,虽肝脑涂地,亦要促成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