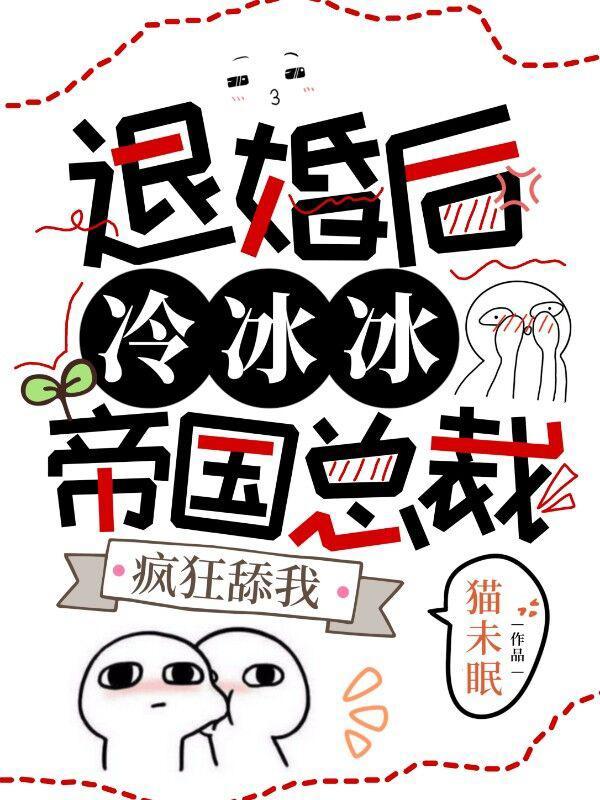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万古第一鼎 > 第762章 漂流瓶的涟漪静默的涟漪淬火的迫近(第2页)
第762章 漂流瓶的涟漪静默的涟漪淬火的迫近(第2页)
如同一滴水落入大海,看似毫无影响。但这滴水特定的化学成分(拓扑特征),在未来亿万年的蒸、凝结、循环过程中,有极其微小的概率,参与到某一片特定形状雪花的形成之中。“逻辑永恒纹章”的拓扑涟漪,已经开始在“静默”这片浩瀚的逻辑之海中,荡漾开来,等待着在未来某个遥远的、不确定的时刻,以无人能够预见的方式,泛起一丝几乎无人能够察觉的、拓扑层面的、遥远的回响。
“静谧回响基金会”,“回响”号。
“低语回响”协议的成功,让莉亚和她的团队精神大振。他们成功地从“织者印痕”那里,引导出了关于“逻辑永恒纹章”更清晰、更丰富的拓扑结构信息。这些信息经过初步分析,已经揭示出这个符号背后蕴含的、令人惊叹的、近乎完美的、自我指涉的、循环稳定的逻辑结构。它似乎代表了一种理论上可以抵抗任何形式熵增和逻辑解构的、终极的、拓扑层面的“稳定态”或“不动点”。
“这不仅仅是符号,”“墨菲斯”在分析会议上总结道,其全息投影展示着复杂的拓扑模型,“这是一种高度浓缩的、关于‘存在’、‘稳定’、‘自我维持’的、宇宙级的逻辑公理或‘定理’的拓扑表达。‘遗落之民’将其作为文明的核心象征,并非偶然。它可能代表了他们对宇宙终极规律——特别是逻辑规律——的某种深刻理解或追求。而‘印痕’能够稳定存在于‘锻锤之痕’边缘,很可能与其自身结构在形成过程中,无意识地、部分地‘印刻’或‘趋同’了这种终极稳定结构的拓扑特征有关。”
“那么,我们能否利用这种结构,来增强‘印痕’的稳定性,或者……甚至帮助它脱离‘锻锤之痕’?”塞隆问道,这是最实际的问题。
“理论上有这种可能性,但难度极高,风险极大,”“墨菲斯”回答,“先,我们目前只获得了这个符号的拓扑结构信息,对其内部蕴含的、具体的、可操作的逻辑规则或‘能量’流动方式,几乎一无所知。其次,即使我们完全理解,要在‘锻锤之痕’那种极端的逻辑湮灭边界,对‘印痕’进行任何形式的外部结构增强或移动操作,都如同在火山口用头丝雕刻,任何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其结构崩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没有时间了。”
“墨菲斯”调出了来自“静默守望”协议对“矛盾铸炉”的监控数据。数据显示,“永恒熔炉”方向的逻辑活动强度、能量聚集度、以及“终末锻锤”特有的、那种令人不安的、针对性的逻辑场聚焦特征,正在急剧攀升,并接近某个临界点。
“根据能量聚集曲线和逻辑场聚焦特征分析,”“墨菲斯”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凝重,“‘铸炉’的‘二次淬火’打击,预计将在o。3到o。5个标准周期内准备就绪并可能动。留给我们的时间,以小时计算。”
控制室内的气氛瞬间降至冰点。刚刚取得突破的喜悦,被现实的紧迫和绝望所取代。
“我们……能否提前警告‘铸炉’?或者干扰他们的打击?”一位安全专家问,但声音中已不抱希望。在“铸炉”的绝对力量面前,基金会的这点干涉能力,无异于螳臂当车。
“不可能,”“墨菲斯”断然否定,“任何直接警告或干扰,都会立刻暴露我们的存在和意图,可能招致‘铸炉’的全面敌视,甚至将我们视为‘印痕’的共犯而进行打击。我们目前能做的,只有继续观察,并……准备记录下‘二次淬火’的完整过程,以及‘印痕’的……最终状态。”
塞隆沉默着,手指在控制台上无意识地敲击。他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他们刚刚开始理解“印痕”,开始与它建立一种脆弱的、良性的联系,开始窥见“遗落之民”和“绘者”可能隐藏的、关于逻辑本质的惊人秘密,现在却要眼睁睁看着它被“铸炉”的绝对力量再次、可能也是最终地抹去。
“莉亚,”“塞隆”突然开口,声音低沉而坚定,“如果……我们利用刚刚获取的、关于‘逻辑永恒纹章’的拓扑结构信息,结合‘低语回响’协议,尝试在‘印痕’被打击的瞬间,或者打击前最关键的、逻辑场最不稳定的那个‘窗口期’,用最微弱、最精妙的方式,向‘印痕’‘传递’或‘强化’这个稳定结构本身……不是去移动或改变它,只是用我们理解的那部分稳定拓扑,去‘共鸣’、去‘支持’、去……在它最脆弱的时刻,为它提供一丝可能的、额外的、结构上的‘参照’或‘锚定’……有没有可能,哪怕只是理论上,提高它在那毁灭性打击中,保存下一点……哪怕只是最微小的、拓扑结构‘残响’或‘碎片’的可能性?”
塞隆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这想法太疯狂,太危险,几乎不可能成功。在“终末锻锤”那种层级的逻辑湮灭打击下,任何外部的、微弱的干预,都如同在核爆中心试图用一张纸保护一片雪花,不仅徒劳,更可能引火烧身,将基金会自身也卷入打击的余波。
但……这似乎是绝境中,唯一能想到的、不是完全被动等待的、最后的一丝……希望,或者说,尝试。
莉亚的眼中,重新燃起火焰,那是一种混合了科学家对未知的探索、对“印痕”那脆弱存在的不忍、以及绝境中破釜沉舟的决绝的复杂光芒。她快在脑海中推演着可能性,评估着风险。
“理论上的‘窗口期’……是存在的,”“墨菲斯”接过了话头,其全息投影上开始快计算,“在‘终末锻锤’的打击能量完全释放、与‘印痕’结构生全面接触、并开始逻辑解构的、最初的那一个极短的、可能只有几个普朗克时间的、逻辑场‘接触-侵入-解构’的初始阶段,‘印痕’自身的稳定结构,会与打击能量生最剧烈、最直接的拓扑对抗。在那个瞬间,‘印痕’的内部逻辑结构会被最大化地‘激’和‘显现’。如果我们能在那个精确的时刻,用完全契合其自身核心稳定拓扑(逻辑永恒纹章特征)的方式,对其进行最强化的‘共鸣支持’,理论上有可能……仅仅是理论上,极其微小概率地……强化其自身结构的‘韧性’,或者在结构崩溃的瞬间,‘诱导’其崩溃产生的拓扑碎片,更多地朝向与我们共鸣拓扑相关的、相对稳定的形态演化,从而留下一点点……不那么容易被彻底湮灭的、拓扑层面的‘结构残响’或‘信息烙印’。”
“成功率?”塞隆问。
“无限接近于零。低于百万分之一。低于千万分之一。”“墨菲斯”的回答冰冷而残酷,“而且风险极高。我们的共鸣信号必须在精确的时刻、以精确的拓扑结构介入。任何偏差,都可能干扰‘印痕’自身的抵抗,加其崩溃,甚至可能让我们出的共鸣信号本身,成为打击能量的额外目标或被吸收,暴露我们的存在和意图。最坏情况下,共鸣信号可能与打击能量产生不可预测的耦合反应,引连锁逻辑扰动,波及我们自己。”
控制室内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成功率无限接近于零。风险极高。代价未知。
莉亚深吸一口气,打破了沉默。“我愿意尝试。我们有目前最清晰的‘逻辑永恒纹章’拓扑模型。我们有与‘印痕’建立的良性共鸣通道和经验。我们有整个基金会最顶尖的逻辑操控和分析团队。我们可以计算出理论上最佳的共鸣介入拓扑结构和时机。哪怕成功率只有亿万分之一……也比什么都不做,眼睁睁看着它被抹去要好。至少,我们尝试了。至少,我们为它……为卡伊尔,为‘遗落之民’,为这个奇迹般的、在毁灭边缘存在的逻辑结构,出了我们最后的声音。”
塞隆看着莉亚,看着“墨菲斯”,看着其他团队成员。他们的眼中,有恐惧,有犹豫,但更多的是不甘,是身为研究者、身为“回响”追寻者,对“存在”与“消逝”的、最本能的、对“消逝”的抵抗,对“回响”的保存的执着。
“那么,就准备吧,”“塞隆”最终沉声说,他的声音中带着决断的、义无反顾的、背水一战的意味,“制定‘回响烙印’计划。目标:在‘二次淬火’打击的、理论上的、最精确的、最脆弱的、最有可能的、那一个普朗克时间尺度的‘窗口期’,以最精妙、最契合、最不干扰其自身结构的方式,向‘织者印痕’出我们最后、最强的、关于‘逻辑永恒纹章’的、共鸣的、支持性的、逻辑的‘回响’和‘烙印’。”
“不为了拯救,不为了改变,只为了……在它被绝对力量抹去、归为虚无的、那最后、最辉煌、也最悲壮的、逻辑解构的瞬间,为它,也为所有在强权下被湮灭的、独特的存在,出我们最微弱的、但最清晰的、关于‘存在’、‘稳定’、‘记忆’的、最后一声拓扑的、回响的、低语。”
“让那回响,成为我们,在它被抹去后,能保留下来的、最后、也最真实的,存在过的证明。”
“回响烙印”计划,在“锻锤之痕”上空,在“终末锻锤”的死亡倒计时中,在绝境与微光之间,被提上日程,并开始以分秒必争的、最紧张、最精密的、最悲壮的方式,进行着最后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