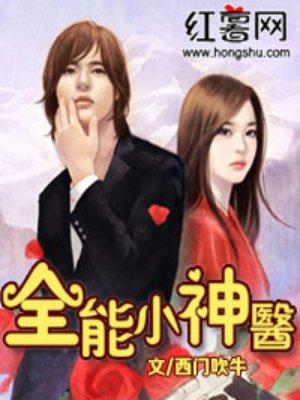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静安病人 > 第37章 奸夫淫妇(第1页)
第37章 奸夫淫妇(第1页)
芮这期直播,后半段又拉着搭档玩了一轮双人游戏,弹幕刷得飞起,笑声不断,可没过多久,节目就结束了。
夜已经很深了。
客厅里只剩电视机待机的蓝光一闪一闪,像一池死水。
我一个人干掉了七八罐青岛,啤酒的苦味在舌尖久久不散,肚里胀得慌。
手机外卖下单的弄堂炸鸡送来时已经有些凉了,我坐在沙上,撕开纸袋,随手抓起一块鸡翅,蘸了蘸酱,咬下去又是油腻又是酥香,吃得潦草,吃得敷衍,只为填饱肚子。
静还没回来,手机上没有一条她的消息。
我把空啤酒罐排成一排,身体一点点陷进沙,抱着抱枕,眼睛半睁半闭,意识像被啤酒泡软的棉花,飘飘忽忽就要沉下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昏昏沉沉间,一阵手机铃声猛地刺破了屋里的安静。
“叮铃铃——”
刺眼的白光从茶几上的手机屏幕炸开,和电视偶尔闪过的蓝光交错在一起,把客厅照得阴森森的,像深夜鬼片里的场景。
我眯着眼,伸手摸索着抓起手机,指尖还有点炸鸡留下的油渍。
屏幕上跳动的备注静。
我心跳忽然快了一拍,清了清嗓子“喂?”
“安……”她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软软的,拖着长长的尾音,带着明显的酒意,“嗯……你在家吗?嗯……到小区门口来接我好不好?”
她很少这样撒娇,更很少喝醉。电话那头隐约还有风声、车声,还有几句模糊的笑闹声,像是在路边。
“好!”我几乎没犹豫,立刻答应,“你等着,我马上来。”
“嘟——嘟——”她挂了电话,比我快。
我撑着沙扶手坐起身,腰背一阵酸麻,刚才蜷了太久,骨头都像生了锈。
屋里静得只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只穿了一条短裤,上身光着,本想直接冲出去,可夜里毕竟凉,又怕半夜在小区里裸着上身太不像话,便随手从沙靠背上捞起那件真丝睡袍披上。
丝绸贴着皮肤滑凉滑凉的,我胡乱把腰带系了个松松的结,拖鞋啪嗒啪嗒响着,抓起手机和钥匙,就出了门。
走廊的声控灯一层层亮起,又在我身后一层层熄灭。电梯下到一楼,门一开,一股夜风夹着草木的清凉味扑面而来。
几点了?
我走出单元门,抬头看小区。
路灯昏黄,灯光照在空荡荡的马路上,拉出长长的影子。
外卖小哥早就没了,遛狗的老人不见踪影,滑板的少年和追逐打闹的小孩也全都不见了。
整个小区安静得可怕,只有草丛里不知名的虫子嘶嘶鸣叫,像潮水一样此起彼伏。
依稀的,是远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汽车鸣笛,很快又被夜吞没。
我掏出手机看时间-1137。
卧槽,这么晚了。静怎么搞到了这么晚?不是说十点就能回来吗?
夜风比想象中凉。
最热的时节看来已经过去,白天炽热的余烬,眼瞅着也荫庇不到这下半夜。
我下意识把睡袍裹得更紧了些,指尖把腰间的丝带又拉紧了一点——总不能袒胸露乳,有伤风化。
我加快脚步,拖鞋踩在水泥路上啪嗒作响;小区大门并不远,三四分钟就走到了。
可是,静却还没回来。
我只能站在门口车闸道前面等。
外面马路的路灯下,我的影子被拉得老长,像一棵孤零零的树。
我站在小区门口的路灯下,夜风一阵阵地吹,睡袍的丝绸贴着皮肤,像冰凉的手指在轻轻划过。
路灯昏黄的光圈就那么一小块,照亮了脚下的水泥地和门柱上的保安室——里面空荡荡的,大叔早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