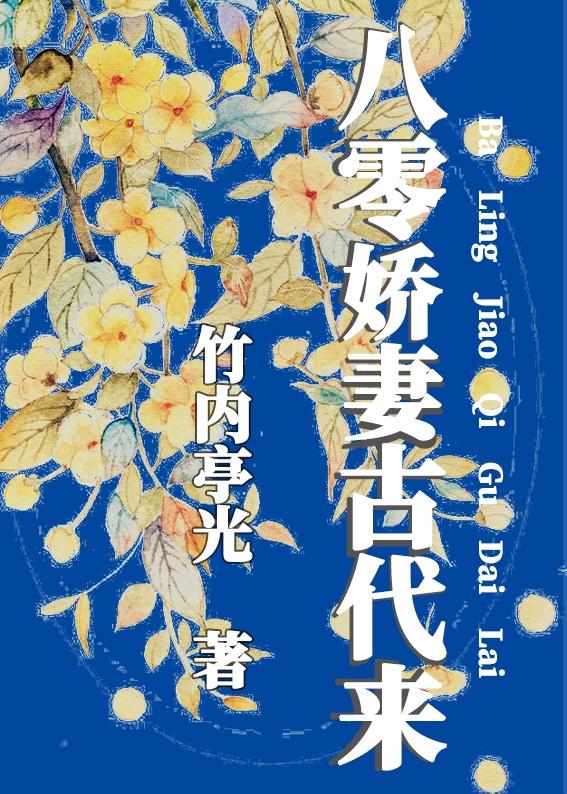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神话三国:刘备手握封神榜 > 第97章 渡口接粮船(第1页)
第97章 渡口接粮船(第1页)
次日清晨,晨雾像揉碎的棉絮,沉在洧水交汇处的水面上,连呼吸都带着湿冷的水汽。
这处渡口的地形生得刁钻,
西岸是连绵的芦苇荡,青灰色的苇秆,被雾裹得只剩模糊轮廓,
风过处簌簌轻响,倒成了最好的掩护;
东岸依着矮丘,坡上杂树横生,枝桠间悬着未散的晨露,落地时轻得像叹息。
三条水道在此交织,主航道宽不过三丈,水面泛着暗绿,水下却藏着深浅不一的暗礁,
只有常年跑船的老艄公,才敢凭着记忆在雾里摸路
——侧航道更窄,仅容一船通行,两岸芦苇密得能遮过人影,正是偷摸行事的绝佳去处。
雾色里,先是浮起点点黑影,顺着侧航道缓缓挪来。
打头的是艘乌篷船,船身被桐油浸得黑,船头立着个裹青布头巾的汉子,手里握着根竹篙,
每一次点在水下都极轻,生怕搅碎了雾的寂静。
紧随其后的,是数百艘甄家舟楫,形制各异却都透着低调:
商户船的船舷,刻着隐晦的“甄”字商号,
原本装绸缎茶叶的货舱被清空,舱板下垫着干草,隐约能看见粮袋的边角;
普通渔船则更显朴素,渔网搭在船舷上,舱里却没见半条鱼,只堆着些伪装用的柴薪,
船尾的艄公,清一色缩着肩,眼神却警惕地扫过四周雾影。
船行极缓,桨叶入水时几乎听不到声响,
只有偶尔碰到芦苇秆,才出轻微的擦碰声。
雾浓得化不开,二十步外便看不清人影,只能凭着前方船尾,挂着的微弱羊角灯辨方向
灯光被雾,滤得只剩一团昏黄,像远处濒死的萤火。
有商户船的船主缩在舱口,手指无意识地摸着,船舷上的木纹,喉结动了动,低声对身边的伙计道:“这雾再浓点才好,就是怕撞着暗礁。”
伙计攥着船桨的手泛白,低声应:“家主说了,跟着前头的灯走,错不了。
甄家的船跑这水道,比走自家院子还熟。”
约莫半个时辰,船队缓缓驶出芦苇荡,眼前豁然开朗些。
此处是渡口的隐秘汊湾,水面平静如镜,岸边泊着三艘更大的粮船,船身漆成深褐色,
船桅上,挂着面暗色旗帜,旗角绣着隐约的“汉”字,正是联军的标志。
粮船周围静悄悄的,只有十几个身着黑衣的士兵立在船舷,腰间佩刀,
袖口绣着细小的“刘”字纹。都是刘备的亲信。
一个个目光如炬,即便在雾里,也能捕捉到百米外的动静。
简雍立在中间那艘粮船的船头,
身着青色儒衫,外罩一件深色短褐,褪去了平日的从容,望向雾中来船。
他身后的亲兵低声道:“先生,甄家的船到了,数目没错。”
简雍“嗯”了一声,声音压得极低:“让弟兄们都警醒些,徐荣的人在下游扎着营,离这儿不过十里地,别出半点声响。”
说话间,甄家的船队已陆续泊岸,
最前头那艘商户船的舱门打开,甄逸走了出来。
他身着素色锦袍,腰间系着玉带,却没了往日颍川支脉家主的气派,面色凝重,脚步轻捷地踏上粮船。
“简先生,”甄逸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急促,“路上还算顺遂,就是雾里行船,慢了些。”
简雍上前一步,握住他的手,指尖能感觉到对方掌心的薄汗。
“逸兄辛苦,”简雍的声音同样低沉,目光扫过身后的粮船,
“这批粮至关重要,主公在前线等着用,迟不得,也错不得。”
他抬手往东南方向指了指,“下游三十里,徐荣的铁骑扎在营里,昨日还派了斥候沿江巡查,
若不是这雾挡着,咱们怕是连汊湾的边都挨不上。”
甄逸叹了口气,走到船舷边,
望着雾蒙蒙的水面,语气里满是商人的谨慎:“先生可知,我这次带出来的,都是甄家最稳妥的船和人。
沿途关卡虽多,靠着商户的身份倒也蒙混过关,但徐荣的人不同——那些西凉兵,眼里只有刀枪,半点情面不讲。”
他顿了顿,声音更低了,“出前,我特意让船工把粮袋都裹上绸缎,对外只说是往江东运的货,生怕走漏半点风声。”
“逸兄的谨慎,我自然明白。”
简雍点点头,眉头未皱,“商人逐利,却也懂唇亡齿寒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