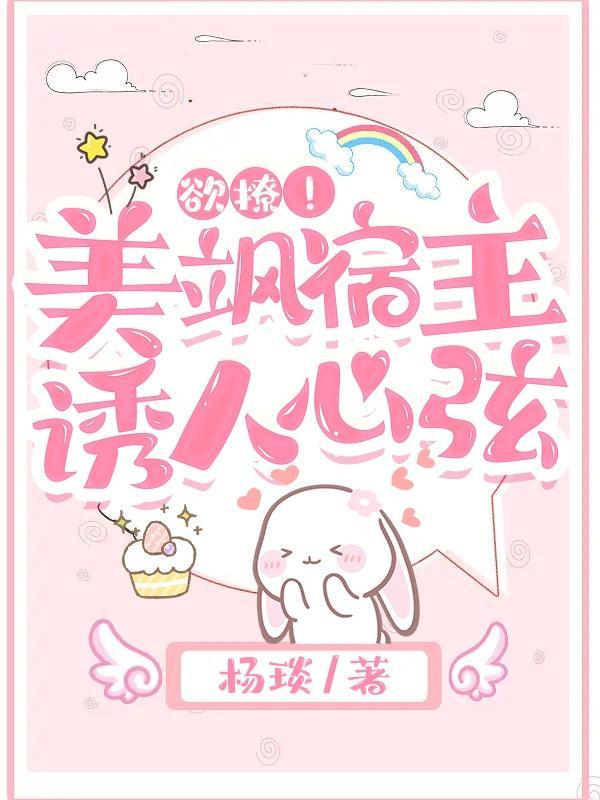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再造山河三十年 > 第171章 东风误我 寒刃春生(第3页)
第171章 东风误我 寒刃春生(第3页)
她要让所有人知道,她还活着,孩子也还活着。她要让那些盼着她死、盼着她流产的人知道,她们失望了。
秋穗应了声“是”,却站在原地没动。
花见羞挑眉:“还有事?”
“回娘娘,”秋穗依旧垂着头,“陛下有旨,说娘娘需要静养,无旨不得出凝香馆,亦不得见外客。太医每日会来请脉,皇后娘娘那边……奴婢们不敢擅自去惊扰。”
软禁。
花见羞的心彻底沉到谷底。陛下不仅降她的位,换她的人,还要将她囚在这凝香馆里,隔绝一切与外界的联系。他是真的不想再看见她了。
“那就去请太医。”她听见自己的声音冷静得可怕,“现在就去。”
“是。”秋穗这才退下。
花见羞重新躺下,拉高锦被盖住自己。被面是崭新的,用的是上好的杭绸,却不再是之前她最爱的绯红色,而是妃嫔才能用的浅粉。连颜色都在提醒她,如今的她已不配用正红、绯红这些彰显地位的颜色了。
她盯着帐顶,脑子里飞快盘算。陛下厌了她,但孩子还是他的骨肉。皇后那边……朱清珞素来以贤德自居,如今掌管后宫,面上不会苛待有孕的妃嫔,但暗地里怎么想就难说了。徐婕妤姐妹定会继续落井下石。其他那些告过状的,见她失势,恐怕也会上来踩一脚。
孤立无援。四面楚歌。
花见羞咬紧牙关。不能慌,绝对不能慌。越是绝境,越要冷静。她现在唯一的筹码就是腹中胎儿,必须用这个筹码,撬开一条生路。
太医来得很快,是个面生的中年御医,姓胡,态度恭敬却疏离。诊脉之后,说的和秋穗转述的差不多:胎象暂稳,但需绝对静养,不可有情绪波动,不可劳累,需按时服药。
花见羞问:“胡太医,依您看,这胎可能保到足月?”
胡太医斟酌着词句:“娘娘放心,只要遵医嘱,好生将养,龙胎定能安康。”
套话。全是套话。花见羞心中冷笑,面上却露出感激的浅笑:“有劳胡太医了。秋穗,看赏。”
秋穗递上一个早已准备好的荷包,胡太医推辞两句便收下了,态度依旧恭敬,却不见半分亲近。
送走太医,花见羞让秋穗去煎药。寝殿里又只剩她一人。
她慢慢坐起来,挪到妆台前。铜镜里映出一张苍白憔悴的脸,眼下有浓重的青黑,嘴唇干裂起皮,原本明媚娇艳的容颜,如今只剩病弱的苍白。
她伸手抚摸镜中的自己,指尖冰凉。
花见羞啊花见羞,你从前何等风光。陛下赞你“容色冠绝后宫”,赏你的珍宝堆满库房,各宫妃嫔见了你都要低头行礼。如今呢?如今你成了才人,被软禁在这一方天地,身边全是眼线,连太医都不愿与你多说半句。
镜子里的女人忽然勾起一抹笑,那笑容冰冷而艳丽,像雪地里开出的毒花。
没关系。都没关系。只要她还活着,只要孩子还在,她就还有翻盘的资本。徐婕妤,花蕊夫人,还有那些告状的贱人……你们且等着。
她拉开妆匣最底层的暗格,里面空空如也。从前这里放着她的体己银票、地契、以及一些不能见光的东西,如今全都不见了。想必是被司卫监的人搜走了。
花见羞也不意外。陛下既然要办她,自然不会给她留后路。好在……她还有别的准备。
她轻轻敲了敲妆匣底板,三长两短。底板是实心的,没有动静。她也不急,从间拔下一根素银簪子,这是她浑身上下唯一剩下的旧物,簪头是一朵小小的玉兰花,花瓣可以旋开。
她旋开花瓣,里面是空的。早在她被下毒那日,簪心里的东西就已经用掉了。
花见羞将簪子重新插回间。没关系,她还有人。钱嬷嬷虽然残了,但还有用。凝香馆里那些被打走的心腹,未必全死了。只要有一个还活着,只要有一个还能联系上……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秋穗端着药碗进来,黑褐色的药汁冒着热气,气味苦涩刺鼻。
“娘娘,该用药了。”
花见羞接过药碗,看也不看,一饮而尽。药很苦,苦得她舌根麻,她却连眉都没皱一下。
“晚膳备了什么?”她问。
“太医嘱娘娘饮食清淡,小厨房备了燕窝粥、清蒸鲈鱼、还有几样素菜。”秋穗答道。
“太淡了。”花见羞淡淡道,“本宫如今需要进补,明日让膳房加一道黄芪炖鸡,一道红枣桂圆羹。若有人问起,就说本宫气血两虚,御医让补的。”
她要吃得好,睡得好,把身子养得壮壮的。她要这个孩子平安健康地出生,要陛下看见这个孩子就想起她。
“是。”秋穗应下,收拾了药碗退下。
花见羞重新躺回床上。夜幕完全降临,宫灯次第亮起,昏黄的光透过素罗帐子,在锦被上投下朦胧的影子。
她听着更漏滴答,一声,一声,敲在心上。
这一夜,凝香馆格外寂静。没有往日的丝竹声,没有宫女内侍走动说笑的细碎声响,只有风穿过廊下的呜咽,和远处宫墙上传来的、模糊的梆子声。
花见羞睁着眼,直到东方泛起鱼肚白。
她的人生,从今日起,是另一番天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