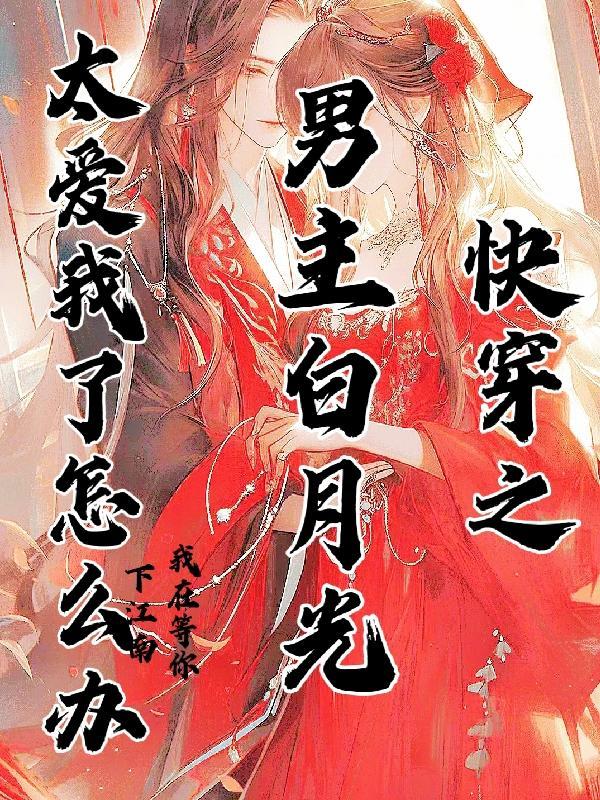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教令院劝退生,提瓦特最强打工人 > 第217章 离得太近(第2页)
第217章 离得太近(第2页)
钟离平静地拾起那根朴实的手杖,目光温和地递还给他。
“小心脚下。”
我这才知道,老者来自远方,专程来璃月港与儿孙团聚,共度海灯节的。
我们一路陪着老者,慢慢走回港口。
虽说是来探亲,但他并未急着去寻找那份世俗的热闹,只是凭栏而立,望着这片被灯火与霄灯点亮的山川与海面。
钟离静立在他身后半步之遥,沉默如同山岩。
港口的灯火倒映在漆黑的海面上,碎成万千金鳞。
老者并未回头,苍老的声音被风送过来:“先生还是老样子,连脚步声都未曾变过。是了……六十年前,我也是这样,在码头的灯火里,听着您的脚步声,等您为我寻回那只被浪卷走的花灯。”
钟离缓步上前,与老者并肩,望向同一片浩瀚的承载了无数记忆的海。
“是你啊。”一如当年,仿佛六十载光阴不过弹指,“多年未见,你的心性,倒还是如幼时那般执拗。”
老者缓缓侧过身,努力仰起头,仔仔细细地端详着那张与记忆中一般无二的容颜。
海灯的暖光为钟离周身镀上一层柔和的金边,却照不亮老者眼中那被岁月沉淀的浑浊。
他抚着银须,笑声沙哑而通透,像是看破了什么:“六十载人间风雪,于我,是爬满额顶的沟壑,是沉入眼底的浑浊。”
“于您呐,却不过是袖角沾染的一粒尘埃,轻轻一拂,便了无痕迹。”
“我垂垂老矣,而您风采依旧啊。”
钟离轻轻摇头,他的目光深邃,仿佛能穿透眼前这具衰老的皮囊,直视那颗曾经属于少年的鲜活的心。
“我所说的,并非指容颜。”他的声音缓缓的,“而是你在此追忆往事的神情。依旧如当年那个,敢与风浪争夺一只花灯的倔强少年,一般无二。”
老者闻言,眼角的皱纹如被春风吹开的涟漪,层层漾开。
那是真正在笑,自心底的笑。
他抬起布满老年斑的手,指尖在昏花的视野里,虚虚地描摹着钟离的轮廓。
“心性未变么……呵呵。只是先生,我的眼已浑浊如磨砂的琉璃,望不清您的轮廓了,只能望见一团,暖玉似的光晕罢了。”他顿了顿,“当年一别,我是走向我的人生,您是走入新的传说。如今我的人生将至终点,而您的传说,依旧看不到尽头啊……”
我默默看着这两位。
忽然一个抱着花灯朝这边跑来的小孩大喊一声:“别追啦阿爹,这灯才不是给你的呢。”
幼童与我们擦肩而过。
这位老者,他光是站着,就像一株被浸透的梧桐。
每一道皱纹里都住着故事。
老者是落在少年肩头的雪,不消片刻便要化去,却偏要教人记住这无常。
神明啊,您让开败的花与初绽的蕾共处于同一阵风。
让溯流的鱼与顺流的水草相望于同一段河道。
这是何等的。。。决绝。
最终,他望着天边缓缓升起的星辰般的霄灯与河边浮着的几朵花灯,喃喃自语,像是说给自己听,又像是说给这片天地听:“能以此身,与您共度两度浮生,我……甚是圆满呐。”
他的目光最后移向我,朝我礼貌而温和地笑了笑,点了点头,算是道别。
他转过身,拄着那根见证了无数时光的拐杖,步履蹒跚地,一步步融入了港口流动的人潮之中,再不见踪影。
“钟离先生。”
“怎么了?”
“……没什么,我们回去吧。”
晚上,到底还是被卯师傅留在了万民堂。
他红光满面,说什么也要钟离先生一起留下吃顿便饭。
“钟离先生,您可得尝尝我新琢磨的这道海灯全家福。”
所以香菱时刻构思新菜是随了卯师傅啊。
饭桌上自是热闹。
香菱叽叽喳喳说着她这段时间的所见所闻,锅巴在桌下钻来钻去。
不对,怎么感觉它在盯着钟离先生看。
卯师傅不停地给我们布菜。
钟离先生偶尔点评几句菜肴,引经据典,听得卯师傅连连点头。

![当虐文反派穿进甜文[快穿]+番外](/img/345948.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