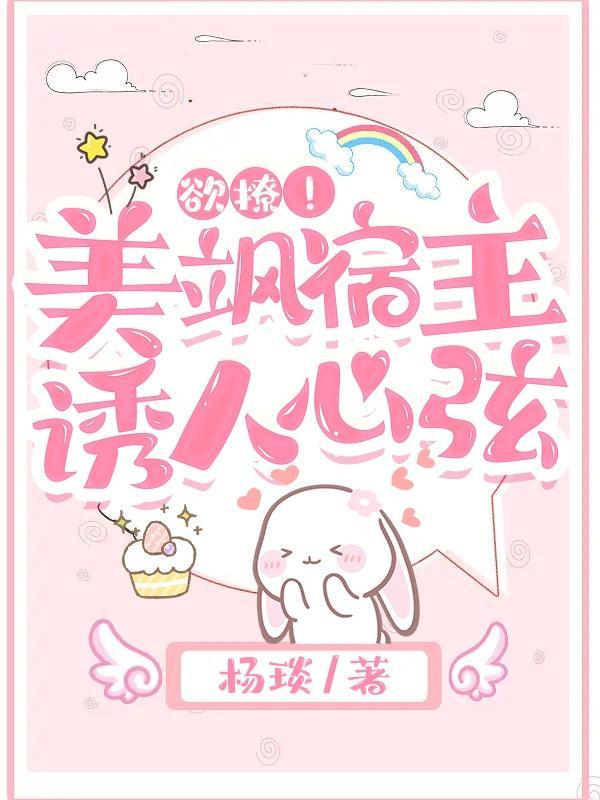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三国:玄行天下 > 第175章 九重诏下战云翻(第8页)
第175章 九重诏下战云翻(第8页)
“诺!”
“其余兵马,”袁绍转过身,目光扫过帐中众人,“随我继续围困易京。但攻势放缓,以困为主,以攻为辅。待击退简宇,再破此城不迟。”
“主公英明!”众人齐声应道。
袁绍摆摆手:“都去准备吧。”
众人行礼退出。大帐中,只剩下袁绍一人。
他走到帐外。夜幕已降,星斗满天。北方的春夜,寒意依旧刺骨。远处易京城头,隐约可见零星的火把光亮,那是公孙瓒的守军在巡夜。
更远处,南方,是黄河,是简宇正在赶来的二十万大军。
“简宇……”袁绍喃喃自语,呼出的气息在寒夜中凝成白雾,“十年前在雒阳,你不过是个小角色罢了。如今,竟敢率军来攻我……”
他握紧了腰间的思召剑剑柄。
剑柄冰凉,凉意透过掌心,一直传到心里。
这一战,他不能输。
输了,就什么都没了。
四世三公的荣耀,雄踞河北的霸业,问鼎天下的野心……统统都会化为泡影。
“我不会输。”袁绍深吸一口气,眼中寒光闪烁,“绝不会。”
他转身回帐。
帐中,火把依旧在燃烧。那火光跳动,在墙壁上投下摇曳的影子,像是无数鬼魅在舞蹈。
而千里之外,简宇的大军,正在星夜兼程,向北而来。
这场决定北方命运的大战,在这一天,终于全面拉开了序幕。
四月初三,渤海郡,南皮城以南五十里。
时值暮春,冀东平原的旷野上,麦苗已抽出一尺来高,绿油油地铺满大地。这本该是农人忙于春耕的时节,此刻却不见一个农夫。唯有成群的乌鸦在低空盘旋,出嘶哑的啼鸣,仿佛已嗅到了死亡的气息。
地平线上,烟尘滚滚。
先是点点黑影,继而连成一片,最终化为一道移动的黑色浪潮。那是青州军的前锋,约八千步卒,由高顺统领。他们着青黑色皮甲,持长矛大盾,队列整齐如刀裁斧劈,行进间除了沉重的脚步声和甲叶摩擦的哗啦声,再无半点杂音。队伍最前方,一面“高”字将旗在春风中猎猎作响。
高顺骑马走在队。他年约四旬,面容刚毅如石刻,下颌留着短髭,一双眼睛沉静无波,仿佛眼前不是即将厮杀的战场,而是寻常行军。他未着华丽铠甲,只穿一件半旧铁札甲,外罩青袍,头上戴着普通的铁胄。唯有手中那杆陷阵枪,乌沉沉的枪杆上布满细微的划痕,昭示着它经历过的无数搏杀。
“报——!”一骑探马从前方疾驰而来,马蹄踏起滚滚黄尘,“将军!前方十里,现袁军!约一万五千人,正列阵而来,旗号是‘袁’!”
高顺勒住战马,举起右手。身后八千步卒如同被无形的线扯住,齐刷刷停下脚步,动作整齐划一。
“再探。”高顺声音平静,“看清主将何人,何种阵型。”
“诺!”探马拨转马头,绝尘而去。
高顺缓缓策马向前,登上一处缓坡。极目望去,只见北方地平线上,一道烟尘正在迅接近。烟尘中,隐约可见密密麻麻的人影和旗帜。
“袁谭……”高顺低声自语,“果然沉不住气。”
副将牛盖策马上前,低声道:“将军,敌军倍于我,是否暂避锋芒,等张辽将军主力到来再战?”
高顺摇头:“张将军命我为前锋,便是要我挫敌锐气。若见敌便退,要我等何用?”
他顿了顿,接着补充道:“何况,袁谭此人,志大才疏,好谋无断。兵虽众,不足惧。”
他调转马头,面向己方军阵。八千步卒鸦雀无声,八千双眼睛齐刷刷看向他。
“诸君。”高顺的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前方,便是袁绍长子袁谭,率一万五千人来迎。你们怕吗?”
沉默。
然后,不知是谁第一个嘶吼:“不怕!”
“不怕!不怕!不怕!”
声浪如潮,震得麦田里的绿浪都为之起伏。这些青州兵,有原本的青州军,有投降的曹军旧部,有黄巾收编的士卒,成分复杂。但此刻,在高顺麾下数月整训,他们已成了一支纪律严明、令行禁止的铁军。
高顺点点头,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但眼中闪过一丝满意的光。
“布阵。”
两个字,简洁有力。
令旗挥舞,鼓角齐鸣。八千步卒迅变阵。最前方是三层重盾兵,大盾砸入泥土,盾牌间隙伸出长矛,如钢铁刺猬。盾兵之后是三排弓弩手,箭已上弦,弩已张机。再后是长枪兵、刀斧手,层层叠叠,形成一座坚实的方阵。
高顺立马阵前,浑铁枪斜指地面。春风吹动他的青袍,也吹动身后那面“高”字大旗。他如同一块礁石,静静等待浪潮的到来。
北方,烟尘越来越近。
袁谭骑在一匹黄骠马上,身着华丽的明光铠,外罩锦袍,头戴狮盔,腰佩宝剑。他年约三十,面容与袁绍有六七分相似,但眉眼间少了那份久居上位的威仪,多了几分浮躁与骄矜。此刻,他望着前方严阵以待的青州军阵,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不过八千步卒,也敢挡我大军?”袁谭声音里满是不屑,“高顺?无名下将,也配与我为敌?”
身旁,谋士辛评策马上前,低声道:“公子,高顺虽名声不显,然观其军阵,严整异常,不可小觑。不如稳扎稳打,徐徐图之。”
“徐徐图之?”袁谭眉毛一挑,“父亲令我守渤海,若连这八千人都拿不下,有何面目去见父亲?”
他拔出佩剑,剑锋在阳光下闪着寒光:“传令!全军进攻!我要一战击溃此敌,生擒高顺!”
“公子三思!”另一侧,将领汪昭急忙劝阻,“敌军列阵以待,以逸待劳。我军长途奔袭,人马疲惫,不如先扎营休整,明日再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