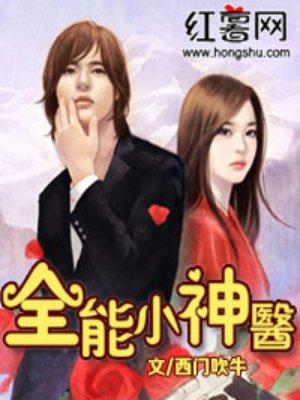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小可怜他被变态包围了 > 第287章 恶鬼与恐怖小说家5(第1页)
第287章 恶鬼与恐怖小说家5(第1页)
午后的阳光透过凶宅积灰的窗棂,筛下细碎的光斑,落在地板的裂缝里,勉强驱散了几分盘踞百年的阴寒。
白祈坐在床边,指尖轻轻摩挲着掌心那道浅浅的疤痕——昨夜激活符文时,指尖被烫出的伤口已愈合大半,却像一枚烙印,刻着昨夜的惊险与此刻心头的温热。
他换了件米白色的薄毛衣,领口松松垮垮地挂在肩头,衬得脖颈愈纤细白皙,皮肤在阳光下泛着近乎透明的细腻光泽。
浅褐色的眼眸清澈明亮,带着一丝刚睡醒的惺忪,长长的睫毛垂落时,在眼睑下投出淡淡的阴影,像蝶翼轻振,模样娇软又干净,却藏着历经多个世界打磨出的沉稳。
墨渊坐在对面的梨花木椅上,纯黑的长袍下摆垂落在地板上,没有一丝褶皱。
他周身的阴寒之气已淡得几乎察觉不到,苍白的脸颊在阳光下显得愈清隽,却少了几分邪魅,多了几分沉郁的寂寥。
他的目光落在白祈身上,猩红的眼眸里没有了往日的探究或警惕,只剩下浓得化不开的温柔,像在凝视一件失而复得、捧在手心怕摔了的珍宝。
“感觉怎么样?”
墨渊开口,声音低沉磁性,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那是昨夜强行挣脱地下封印时,被怨气反噬留下的痕迹,“指尖的伤还疼吗?”
白祈摇摇头,浅浅一笑,樱粉色的唇瓣微微上扬,眼尾泛起一丝娇俏的弧度:“已经不疼了,谢谢你昨晚守着我。”
他顿了顿,指尖依旧摩挲着掌心的疤痕,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道,“昨天那只黑猫,还有古籍里的怨灵,到底和你是什么渊源?我能感觉到,你对它们的情绪,不只是厌恶。”
墨渊的目光骤然暗了下去,猩红的眼眸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像被搅乱的墨汁,有痛苦,有怨恨,有不甘,还有一丝深不见底的疲惫。
他沉默了许久,久到阳光都悄悄移动了位置,才缓缓开口,声音带着穿越千年的厚重与沙哑,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深处碾过:“那是我生前的血海深仇,纠缠了我整整一千年。”
“生前?”
白祈的身体微微前倾,浅褐色的眼眸里满是认真,没有丝毫畏惧,只有纯粹的倾听与关切,“你以前……是活生生的人,对吗?”
“是。”墨渊点头,指尖无意识地划过椅子扶手,那里还留着千年岁月刻下的细纹,“千年之前,我是大靖王朝镇守雁门关的大将军,墨渊。”
千年之前的大靖,江山飘摇,北境狼烟四起。匈奴铁骑如饿狼般频繁南下,踏碎了边境的炊烟,掳走了无数百姓,千里沃土沦为焦土,哀嚎声日夜不绝。
彼时的墨渊,还是个未满二十的少年郎。他出身将门,自幼在军营长大,父亲是战死沙场的老将军,母亲早逝,唯一的牵挂便是麾下的将士与身后的国土。他熟读兵书,弓马娴熟,一杆银枪使得出神入化,年纪轻轻便练就了一身铜皮铁骨。看着边境百姓流离失所、尸骨遍野,他毅然上书朝廷,自请出征,带着父亲留下的旧部,驻守雁门关。
那时候的他,眼里有光,心中有火。身披亮银甲,腰悬青锋剑,站在雁门关的城楼上,望着关外茫茫戈壁,许下的誓言掷地有声:“定护大靖河山无恙,护百姓安居乐业。”
他说到了,也做到了。
匈奴来犯,他身先士卒,率领将士们冲锋陷阵。战场上的墨渊,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战神。银枪划破长空,染满了敌人的鲜血,却从未有过一丝颤抖;铠甲被箭矢洞穿,伤口流血不止,他依旧咬牙坚持,嘶吼着指挥将士们反击。有一次,他为了救一名被匈奴围困的小兵,硬生生扛下了三刀,后背的伤口深可见骨,军医都说他活不成了,他却靠着一口硬气,躺了三天三夜便又爬了起来,再次提枪上了战场。
他体恤将士,从不摆将军的架子。将士们冻着了,他便把自己的狐裘分给大家;粮草断绝时,他便和将士们一起啃干硬的饼子,喝浑浊的河水;有将士战死,他亲自为其收敛尸骨,对着墓碑三叩九拜,哭得像个孩子。麾下的将士们都心甘情愿为他卖命,说“跟着墨将军,死也值了”。
几年时间里,他率军收复失地千里,斩杀匈奴领,逼得匈奴签下城下之盟,承诺十年内不再南下。边境终于迎来了安宁,百姓们感念他的恩情,自为他立生祠,香火不断,称他为“护国神将”。就连远在京城的皇帝,也下旨嘉奖,称他为“大靖栋梁”,赏赐了无数金银珠宝,还有这座位于城郊的将军府。
那是墨渊一生中最耀眼的时光。他以为,只要自己忠心耿耿,守住这江山,就能换来君臣和睦,百姓安宁。可他忘了,皇权之下,最容不得的,便是“功高盖主”。
随着他的威望越来越高,民间只知有墨将军,不知有皇帝的流言,像野草般疯长,渐渐传到了京城的龙椅上。
皇帝是个多疑之人,年轻时靠着弑兄夺位才坐稳江山,如今看着墨渊手握重兵、威望无双,心中的猜忌便像毒藤般疯狂滋生。他开始处处提防墨渊,先是收回了他的部分兵权,又派亲信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甚至在他的军中安插眼线,四处搜罗他“谋反”的证据。
墨渊对此一无所知。他依旧一心为国,把皇帝的赏赐悉数分给将士和百姓,自己依旧过着清苦的日子。将军府里空荡荡的,除了必要的陈设,没有一丝奢华,与普通百姓家无异。
匈奴撕毁盟约,再次举兵南下的消息传来时,墨渊毫不犹豫地再次主动请缨。他以为,皇帝会相信他的忠诚,会派援军支持他。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次,他踏上的,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死路。
那一战,打得异常艰难。匈奴设下埋伏,将墨渊的军队困在了雁门关外的野狼谷。山谷两侧是悬崖峭壁,谷底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易守难攻。匈奴人断了他们的粮草和水源,日夜轮番进攻,将士们一个个倒下,活着的人也都面带菜色,疲惫不堪。
墨渊坚守了七天七夜。这七天里,他写了十二封求救信,派人突围送往京城,却石沉大海,没有一丝回音。他不知道,那些求救信,全被皇帝扣了下来;他不知道,皇帝早已下了密旨,要将他和他的将士们,全部灭口在这野狼谷中,然后对外宣称他“勾结匈奴,背叛朝廷”。
第八天清晨,匈奴人起了总攻。墨渊的银甲早已被鲜血染透,伤口化脓炎,疼得他几乎晕厥,却依旧死死握着那杆陪伴他多年的银枪,嘶吼着指挥将士们反击。他的副将,也是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林风,挡在他身前,手臂被匈奴人的长刀砍断,鲜血喷涌而出,却依旧笑着对他说:“将军,别怕,兄弟们还在!”
就在他们拼尽全力,即将冲出山谷的那一刻,身后突然传来了熟悉的号角声。墨渊心中一喜,以为是援军到了,可回头望去,看到的却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那是皇帝派来的“剿贼军”。
“墨渊勾结匈奴,背叛朝廷,陛下有旨,格杀勿论!”为的将领高声喊道,语气冰冷,没有一丝人情味。
话音刚落,无数支冰冷的箭矢便朝着他们射来。
那些箭矢,来自他们誓死守护的大靖,来自他们效忠的皇帝。
“将军!小心!”林风嘶吼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扑到墨渊身前,为他挡下了致命的一箭。
箭矢穿透了林风的胸膛,鲜血溅了墨渊一脸。林风的身体软软地倒在他怀里,眼睛睁得大大的,里面满是难以置信和不甘,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只吐出了一口鲜血,最后看着墨渊,艰难地挤出几个字:“将军……活下去……为我们……报仇……”
说完,他的头便歪了下去,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林风!”墨渊嘶吼着,声音嘶哑得不像人声。他抱着兄弟冰冷的尸体,看着身边的将士们一个个倒下,被自己人的箭矢穿透胸膛,心中的痛苦和愤怒像火山一样爆。
他想不通,他一生忠君爱国,从未有过二心;他的将士们,一个个都是忠心耿耿的好汉,为了守护这江山,抛头颅洒热血,却为何要落得如此下场?
匈奴人见状,趁机起进攻。墨渊的军队腹背受敌,很快便溃不成军。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将士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看着他们的尸体被匈奴人践踏,心中的信仰彻底崩塌。
他红着眼睛,提着银枪,像一头失控的野兽,朝着皇帝派来的“剿贼军”冲去。银枪翻飞,鲜血四溅,他杀红了眼,不知疲倦,不知疼痛,身上又添了无数道伤口,却依旧没有停下。
最终,他杀出了一条血路,带着满身伤痕,逃出了野狼谷。
可他却成了朝廷通缉的“叛贼”。
他不敢回京城,不敢见亲友,只能四处逃亡。曾经的“护国神将”,如今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叛徒。他一路上受尽了白眼和唾弃,有人向他扔石头,有人朝他吐口水,骂他“卖国贼”“白眼狼”。
他辗转回到雁门关,想看看那里的百姓,想告诉他们真相。可他没想到,那里的百姓,早已被朝廷的流言误导,对他避之不及。有个曾经受过他恩惠的老婆婆,甚至拿起拐杖打他,哭着说:“我们看错了你,你这个叛徒!”
那一刻,墨渊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彻底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