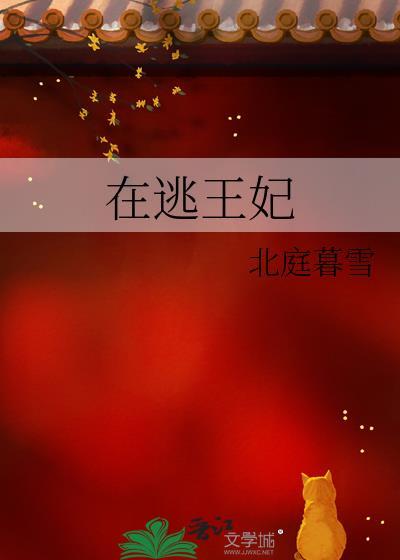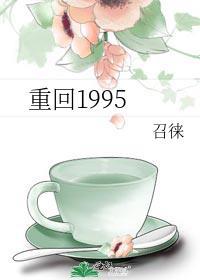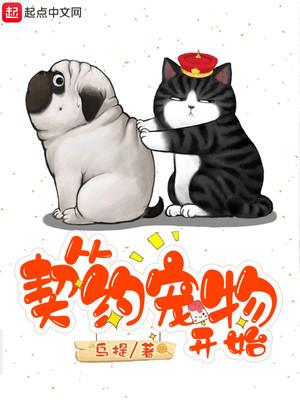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八零有喜:糙汉的锦鲤小媳妇 > 第166章(第1页)
第166章(第1页)
第166章
腊月二十八,年关的气息如同浸染在冰冷空气中的稀薄糖香,若有若无,北风刮在脸上,带着干冷的刺痛感。
苏晚坐在工作室里,面前摊开着省城方经理寄来的最新一封电报,以及一叠来自邻镇和县里零星客户的订单。炭盆里的火偶尔噼啪一声,爆出几点火星,却驱不散她心头的寒意。电报上的措辞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急切,方经理提到,海外客户对“竹韵”系列的反响超出预期,催促她尽快提供更多设计,并询问“晚衍”是否具备承接更大批量订单的能力。
能力?苏晚指尖无意识地划过电报纸上那个“大批量”的字眼。以“晚衍”目前五个人的规模,维持现有的精品定制和小批量工装已是满负荷运转。扩大规模,意味着需要更多的场地、更多的设备、更重要的是,更多可靠且手艺过关的工人。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而另一边,县轻工局郑副局长那看似放手、实则余威犹在的“期待”,像一片阴云,悬在头顶。她深知,官方的好意,有时比明面上的恶意更难应对。拒绝了一次,难保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方式或许会更加“巧妙”。
“晚晚姐,你看这账目。。。。。。”春妮拿着一本新誊抄的账册进来,脸上带着几分忧色,“这个月买好料子的钱支出多了不少,虽然省城那边的定金到了,但周转还是有点紧。王婶那边互助小组的几个嫂子,也想问问,年前能不能先把上回做垫肩的分红结了,大家等着办年货呢。”
钱。苏晚揉了揉眉心。扩建工作室需要钱,添置缝纫机需要钱,支付工钱和分红需要钱,收购更多优质布料也需要钱。省城的订单利润高,但回款周期长;县里和镇上的订单稳定,但单价有限。“晚衍”像一棵正在抽条拔节的树,每一寸生长都需要养分,而根基下的土壤,却远未到肥沃无忧的地步。
“先把互助小组的分红算出来,按时发下去。”苏晚定了定神,对春妮说,“信誉比金子还重要。料子钱的事,我再想想办法。”
春妮应声去了。苏晚站起身,走到窗边。院子里,陆衍正和王叔一起,将新买的几根粗壮檩木抬到东边空地上,那是开春后预备扩建工作室的地基。两个男人喊着号子,沉重的木头在他们肩上仿佛轻了许多,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一团团散开。
陆衍似有所觉,抬起头,目光穿过院子,与窗内的苏晚对上。他没有说话,只是朝她微微点了点头,那眼神沉稳依旧,带着一种“有我在”的安定力量。苏晚纷乱的心绪,奇异地平复了些许。
然而,现实的困境并不会因一个眼神而化解。下午,苏晚去公社信用社咨询贷款事宜。接待她的信贷员倒是客气,但听到“晚衍”只是个个体户,想要贷款扩建厂房和购买设备时,脸上便露出了为难之色。
“苏晚同志,不是我们不支持你,”信贷员推了推眼镜,“实在是政策有规定,对个体经济的贷款,额度有限,而且需要足够的抵押或者担保。你们这。。。。。。主要是靠手艺,这厂房设备,也不好估值啊。。。。。。”
最终,只批下了一笔数额很小的贷款,对于苏晚的计划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从信用社出来,寒风卷着地上的碎雪末,打在脸上。苏晚裹紧了棉袄,心里沉甸甸的。她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个人力量的渺小。纵然她手艺精湛,有想法,有魄力,但在现有的制度和环境下,想要做大做强,每一步都走得如此艰难。
“哟,这不是苏大老板吗?怎么,也来信用社借钱?”一个略带尖刻的声音自身后响起。
苏晚回头,看见孙小曼穿着一件崭新的红色呢子大衣,拎着个皮包,正从信用社里扭着腰肢走出来,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讥诮。她身边还跟着一个穿着干部服的中年男人,苏晚认得,是公社供销社的一个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