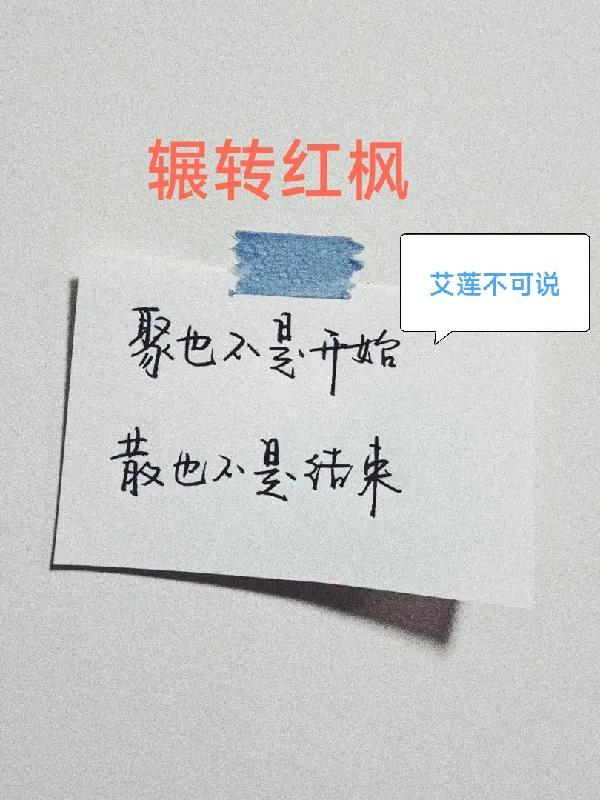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误入春深 > 第七章 查案(第7页)
第七章 查案(第7页)
豫怀稷低眸看会儿她,抓握她的手轻微松开:“理由?”
熟识他的人都晓得,他怒算不得真可怕,挖苦人时也还凑合,唯独他吐字简短,一字一词向外扔的时候,才是顶吓人的。
宋瑙不敢瞧他,只死捏住他袖子一角,不错眼珠地注视桌面:“之前在华阴坡,盗墓的摸出一支簪,说是差使他们的人给作定金用的。那簪子我见过,通体莹白,顶头有粒鸽子血,我年幼时陪堂哥到莫府下聘,它曾插在莫大小姐的髻上。”
少年人的喜恶总摊在表面,当年她欢喜这簪子,还没出莫家,就缠上宋晏林买给她。
宋晏林找借口拒绝:“你这年纪,压不住。”
宋瑙见招拆招,提出:“你先买了,我再长两年,总能压住的。”
那时的宋晏林,眉目里找不到喜气,常年含笑的唇也收起弯弧,抿成直线:“那等你长两年,找你丈夫买去。”连调侃也淡淡的,“真当堂哥冤大头了?”
宋瑙两手叉腰,问他:“你有钱娶媳妇,没钱给小妹买一支新簪,这说得过去吗?”
“哪里过不去?”宋晏林淡定地反问,“我脸皮厚,你的也不薄,咱们半斤对八两,谁也别怨谁。”
宋瑙登时词穷,居然还认为有些道理。
莫府的庭院种了几棵白千层,凉风吹过,吹散一树的白绒毛。
宋瑙在沙沙的风中听见女子若隐若现的低笑,她想要回头,却被堂哥一巴掌抵住后脑勺儿,将她的头往下压。视野受阻,她只能看见青灰的石板,与脚底铺散的白絮。
之后宋晏林解释,按她头,是手滑。但他的屁话,宋瑙一句不信。
那天,她就记住那支白玉簪,和临走时顺风传来的,不太像莫大小姐的轻笑。
“可我想着,女子簪多有相似,许是碰巧了。”宋瑙依然抓得很紧,把豫怀稷的袖臂抓出褶皱,“但乞巧节当晚,有人在湖畔撞到我,她跑到人群外,有三两个瞬间,我几乎以为莫姑娘活过来了。同样穿着夹竹桃花色的夏衣,人很瘦,窄肩薄背,我是追她才迷的道,她跑得很快,是在莫家老宅附近不见的。”
安静地听她说到这里,那晚的全貌越加清晰。
“你也是在她走后,遇到的徐斐?”豫怀稷语气很平静。
宋瑙始终低垂脑袋,做错事的样子:“陆公子说得对,他们引的不单是徐斐,我也在一些人的设计中。”她讷讷地说,“有温萸在,她有的是法子鼓动徐斐前来提亲,但我必不肯嫁,而徐斐是国舅,我能指望的只有王爷了。”
后头的话,豫怀稷接着她的说完整:“他们想透过你的口,像现在这样,引起我对莫恒旧案的注意。”他冷呵,“打得一手好算盘。”
他的音调依旧没什么起伏,但语气已降到冰点,叫人有点喘不过气。
宋瑙还想再说什么,门外再度传来脚步声,顾邑之已去而复返。
他说,叶鄂水死了,这原也不足挂齿,只是仵作在叶鄂水耳根找到一块古怪的印记,纹路刺进皮肉里,擦洗不去。周县令认为不大寻常,就喊顾邑之来看上一眼。
“几根直线拼接在一起,呈暗红色,类似于图腾,看伤口的形态,存在有小两年了。”
宋瑙听得一怔,她依稀记得,她伤到腿那会儿,豫怀稷登门看望,曾给她过目了一张纸,上面画的图案奇异,跟顾邑之的描述很接近。
“顾夫子以为,那会是什么?”豫怀稷面向他,手臂收拢,将袖子从宋瑙攥起的掌心中抽走。
顾邑之思忖道:“某些角度,有点像星宿图,但具体有什么含义,无从得知了。”
由他一点,像找到点门道,宋瑙回忆起那个鬼画符来,拿星宿去对比,倒也神似。
“我该留他一口气的。”豫怀稷摆头,“杀早了。”
但死都死了,没有重来的可能,加上在顾邑之这儿得来的消息波及面太广,他需要单独消解一下,便拒绝周县令的留饭,先行离去。
宋瑙亦步亦趋跟在他身后,往常走在长街上,豫怀稷总会牵住她,但这次并没有,也没刻意去迁就她的脚步,走得比平日快不少。
宋瑙因为瞒他的这些事,内心本就不大安定,现在见他一反常态,各种可怕的后果挨个蹿出来,眼眶咻地红了。
顾邑之要回去照料儿子,也同他们一块儿出的门,转眼就现点问题,豫怀稷腿长脚长的,宋瑙落在后头,要不时小跑才能缩短间距。
顾邑之观测小半天,在快要走到岔路口时,他加紧步子,到豫怀稷肩侧快低语。
宋瑙正专心追赶,还没听见什么,豫怀稷已转过身,目光终于扫在她头顶。
男人一靠近,宛如一颗切开的大洋葱,熏得她泪腺崩坏,眼泪簌簌地掉。想到自她认识豫怀稷起,就没受过适才那样的冷落,不由得悲切哽咽:“你、你是不是想跟我和离了?”
豫怀稷叹口气,抬袖给她擦泪,幽幽道:“不带这么诬陷人的。”
可她受到挫伤了,哄不好的那种,这时顾邑之已默默走出岔道,他点到即止,不再干扰别人家务事。
豫怀稷环顾周围,没见酒楼一类可以停歇的地方,便拉宋瑙进了家古董铺子,向老板借用招待商客的区域。
“你这地儿不错,我惹我家娘子伤心了,借你的风水宝地一用,说完话就走。”
老板是见人下碟的主儿,看豫怀稷通身贵族气派,立即应允了。
豫怀稷把小姑娘按坐在酸枝木椅上,绕到前方,半蹲着给她擦泪。
“怨我。”他轻声赔不是,“只顾想事情了,是我疏忽,我的不对。”
宋瑙抽抽噎噎的,打出一个哭嗝来:“你生我气了,你都不等我,你不想同我过了。”
她一连串的控诉,逐句加重,弹珠似的向外丢,豫怀稷无奈地举起右手,跟她誓:“我媳妇天上有地下无,娶到即赚到,我这么好运道,谁会不想过?”
可凡人的情绪,尤其是忐忑同委屈,来时如山倒,去时如抽丝,宋瑙显然还压在山下,哭得鼻尖通红:“我不是故意瞒你的。”她用力摇头,小声凝噎,“他们想利用我传话,我怕、怕有陷阱,害到你。”
这铺子半天没个访客进出,老板在柜面里盘点物品,安静得只能听见她的抽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