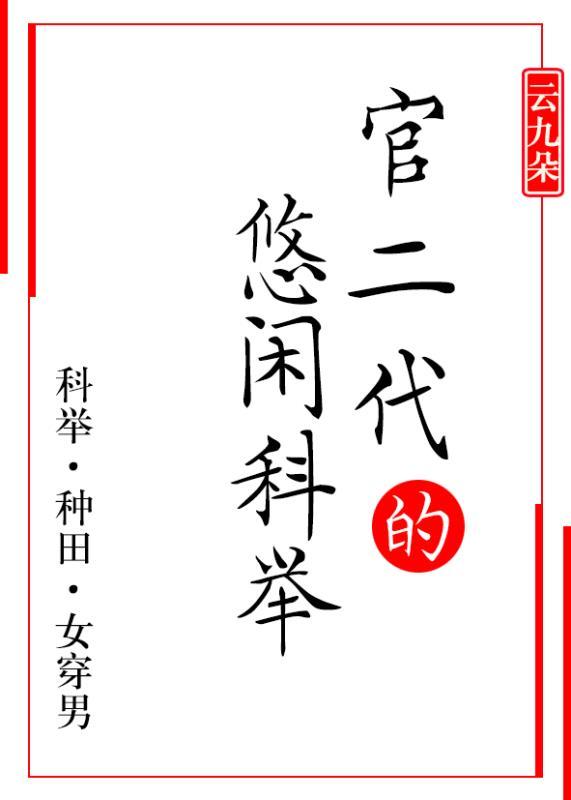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误入春深 > 第四章 相护(第8页)
第四章 相护(第8页)
宋瑙怕他年纪轻轻气出个好歹,轻咳一下打住了。她看见王府门前有两匹大马,一副整装待的样子,便问:“王爷与陆公子是有事要出门去?”
陆秋华缓过来一点,刚要说去点兵场,豫怀稷抢话道:“没有。”拍一拍陆秋华肩膀,“日头不错,陪他出来晒一晒,身上一股子霉味。”
他吩咐戚岁:“去大狱外头候着,徐斐一出来,带他去福如酒家见我。”
戚岁离开后,陆秋华冷冷笑起来,大抵是担心多说多受气,他一声不吭地翻身上马,看豫怀稷把未来夫人送上马车,然后才跃上白龙驹。
福如酒家离王府只有半炷香的脚程,他们到得早了。豫怀稷头一件事便招呼店小二搬来一扇绣面屏风,挡在宋瑙与一会儿留给徐斐的空地之间。她的正面视野受阻,老老实实地说:“这个有点挡视线。”
“他在牢狱污秽地待了这么些天,脏得很,有什么可看的,不怕长针眼?”
豫怀稷目的明显,下手果断,宋瑙无奈地噤声。
会不会生针眼她不大确定,但此人心眼只有针尖大小,她却是深有体会。
徐斐午时出狱,过来也要段时间,豫怀稷点了一桌菜,全是样式精巧,吃起来不会太狼狈的。宋瑙闷头吃着,有一句没一句地听豫怀稷跟陆秋华闲话等会儿去点兵场的事。
忽地,一双筷子往她碗里放了两片糯米糖藕。这盘子是搁在陆秋华手边的,离宋瑙比较远,她一直没去动筷子,豫怀稷注意到了,给她夹来一些:“今日兴致不高?”
虽为疑问句式,但用的则是陈述语气,宋瑙的确还没从前些天宋晏林的造访中完全抽离出来,但她稍加掩饰过了,没料着豫怀稷会这么快瞧出来。
幸而她吃得认真,口中是还没咽下的素鸭,左手持勺舀满玉米,右手的筷子上已经火叉起一块糖藕,一副腾不出口去回答他的无辜样子。
而眼见她前方那道青豆玉米,适才筷子一夹一个准,挑得只剩下青豆了,豫怀稷大方伸手,抽走陆秋华面前他正欲下筷的整盘卤牛肉,跟稀稀拉拉的青豆对调了下。
陆秋华惊愕:“你还是人吗?”
豫怀稷无视他,似不经心地想起什么别的,又问:“宋世子之后有来找过你吗?”
宋瑙僵了僵,一不小心,被刚咬下一口的藕间糖丝糊了一嘴。
听豫怀稷的口吻,非但一早知道宋晏林,应当还有一定关注。宋瑙费力地舔掉糖渣,异常小心地说:“是见过一面,聊了些近况,也没聊太久。”
这话过于笼统,鉴于这人在一些方面惊人的计较,她决定再多说点:“堂哥他有些担忧,王爷是干大事的,怕我嫁去王府不大能应付得好府中庶务,就多嘱咐了几句。”
一番话已经够婉转了,但豫怀稷仍旧透过表象,抓住本质。
“所以说——”他手指一捏,筷子裂成两段,“他想挖我墙脚。”
宋瑙一凛,坚决否认:“绝对没有!”她拍着胸脯保证,“我们老宋家的家风一向以老实本分见长,王爷看我便可知,谁能做出那事来!”
陆秋华本在一旁百无聊赖地吃青豆,冷不丁插嘴:“挖也无妨,有办法的。”他持之以恒地提议,“你娶我小妹,我没那些个顾虑。”
桌上另外两人整齐划一地看向他,豫怀稷预知后事般摇一摇头,原想再趁机问些有关宋晏林的事,可陆秋华这一搅和,给宋瑙拉开个口子,这丫头可不得以攻为守。
果不其然,并不了解自己犯下什么错误的陆秋华只见宋瑙眼中精光飞闪,他没来由地一抖筷子,青豆嚯地掉了下去。宋瑙已经垂下头,手指对手指,尤为可怜地哼唧:“堂哥不过是出于兄妹关怀,提醒则个,陆公子却连下家都替王爷找好了。”她哀怨道,“王爷今日出言责怪,莫非是反悔了,不想娶我了,便拿堂哥当幌子。”
“哪门子的下家,这可别赖我。”豫怀稷含笑接招,“当中的来由戚岁那碎嘴可都跟你交代过了吧。”
“今时不同往日吗?”宋瑙迅回应,“那时八字还没一撇,我当个话本听,如今王爷都下过聘了,以为陆公子应当死心了。”说着,又哀怨地瞟一眼陆秋华,“陆公子长得细皮嫩肉,令妹也必然是个美人坯子,我大概是比不过的。”
陆秋华听完她的形容词,手背青筋跳了跳。
“王爷跟陆公子是同僚,平常在一块儿的时间比我多,自然更疼陆公子一些。”她叹口气,“所以堂哥说几句关照的话,王爷便折筷子翻脸,陆公子这么明目张胆了,王爷都不舍得讲一句。”
原先是放手随她去挥,这下豫怀稷也有些恶心到,寒毛陡然竖起。他看向罪魁祸,冷冷道:“谁说我不讲他的,晚点到兵营,我不仅会讲他,还要揍他。”
陆秋华也恶心了一把,闭眼咬牙:“打死我算了。”
这时,外头传来叩门声,戚岁已经将人带到了。
豫怀稷先作罢,又气又好笑地说:“宋晏林这茬,我下回再问。”
宋瑙喝口茶,润了润嗓,乖巧地点头:“那余下的话,我也下回再说。”
听到她还有没放完的话,陆秋华好不容易夹起来的青豆再次滚到桌下,脑子一阵嗡鸣。
稍作片刻调整,豫怀稷才叫戚岁把人领进来。
徐斐畏畏缩缩地走在前面,身侧跟了个女子,她满面精致浓妆,一进门随之扑来厚重的脂粉味。他们行完礼,见徐斐抖索得厉害,豫怀稷淡然道:“慌什么,问你点事,仔细答便是。”
徐斐在牢里待怕了,拼命点头,恨不得把一家子的老底全都吐出来。
宋瑙坐在屏风后,开门见山道:“徐公子,我有些疑惑,还望公子指教。”客气清冷的话音透过绣布,传至徐斐耳中,“我初次见到公子的时候,地处偏僻,左右皆为普通民居,按说不是找乐子的好去处,这乞巧佳节,公子怎么想到要去那儿的?”
徐斐听她旧事重提,皮肉猛地一收缩,之前挨过的毒打又冲回脑海,顿时语无伦次:“那个,不、不是,我喝酒了,对,我……”
徐斐一慌,舌头便捋不直。豫怀稷沉下脸,在耐性快消耗前,陪同徐斐前来的女子忽然俯身跪下,哭哭啼啼地说:“全是妾身的错,那天少爷多喝了几杯,原本不该出去的,但妾身伺候少爷时间短,只入府一年多,那时还住在沛庄的别院。”
她提袖子拭泪,哭得梨花带雨:“今年第一趟随少爷回帝都,又赶上节庆,妾身小县城来的没见过这么些新奇玩意儿,便缠了少爷去逛庙会。”
意料到会有这个说法,宋瑙垂落杯盏:“往庙会去,怎么走那条道?”
“这也怪妾身不好。”女人把一切都揽下来,“马车驶到北十街时,妾身听车夫说,只要直走往下,见到陈记当铺的招牌左拐,不出一炷香便到离水湖了。”她哽咽道,“妾身没什么见识,那北十街虽远不及主道人多有趣味,但街边十几步一小摊,也比沛庄热闹多了,想着便一路逛去庙会,这才弃车步行。”
宋瑙并无意外,淡淡替她说下去:“然后,走错方向,迷路了?”
女子怯生生地点一点头,不时掸落的眼泪把妆都洇湿了。屏风隔断宋瑙大部分视线,但到底不是封死的,她依稀可以穿过侧面的间隙看见这两人,思索须臾:“是了,我记得你。”
女子是当晚与徐斐同行的女眷,宋瑙若有所思:“你那天妆容没这样浓,乍一眼有些认不出。”
女子一面抽噎,一面从袖子里拿出块干净帕子,按在眼周花妆的一圈,小心抹蹭。
“今儿是接少爷回府的日子,妾身特意装扮得鲜妍点,好给少爷去一去晦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