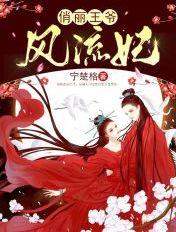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北派寻龙笔记 > 第60章 二踢脚(第3页)
第60章 二踢脚(第3页)
“加大摩擦面积,减缓滑落度!”
“啊?……好好……”
袁大头照我说的,尽可能的张开双腿,两扇屁股蛋死死的贴紧了夯土层。
这招果然有效,下滑的度明显变慢了很多,随着坡度不断变缓,我俩终于停了下来。
“哎呦,老子的屁股……三条你帮我看看,裤裆是不是磨漏了。”
袁大头撅起屁股给我看。
“漏了也没事,墓里除了你就是我,怎么,你还怕墓主人看你腚沟子?”
“谁知道他有没有特殊癖好,还是小心为妙。”
我没闲工夫和袁大头继续扯皮,看着下面的砖石甬道,点了一根烟丢了下去。
烟头的火光在甬道里忽明忽暗,一点熄灭的迹象都没有。
这就说明里面的氧气含量很足,憋不死人。
袁大头很好奇为什么墓里会有氧气,墓主人都死了不知道多少年了,还要氧气干什么,难不成墓葬也要修通风口?
我说:“藩王李璘是唐朝人,唐代的古墓都有修建天井的习惯,而且天井的数量也不是想建多少个就建多少个,殡葬礼法上有明确的要求。”
“这玩意还按需分配呢?”
“可以这么理解,太子七井,公主四井,三品以下的官员仅能享受到一个天井。而且咱俩刚才滑下来的这个斜坡,我估摸着,应该就是藩王墓的其中一个天井。”
袁大头扒拉着手指头,似懂非懂。
其实对于历朝历代的墓葬形式,我也是一知半解。
就比如其中一点,我当时就没想明白。
那就是为什么藩王墓要把天井设计的这么宽,这不明摆着,给盗墓贼提供了天然的盗洞吗?
直到后来,我在考古杂志上看到了一篇关于洛阳龙门唐安菩墓的报道,再重新回想起藩王李璘墓的构造,才有了一点新的思路。
藩王墓没有修在山峦耸立的险峰,也没有修在地势延绵的丘陵。
这个墓葬摒弃了一切风水堪舆的束缚,完全按照金水相生的星象格局进行选址,所以才选择了太子河支流的芦苇荡。
芦苇荡下面有什么?
淤泥。
大量的淤泥。
想要在这种地质环境下,挖出一个地底空腔,几乎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先在四周打上一圈天井,让天井充当运输淤泥的通道,然后一点点从里往外挖,这样才有可能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推测的到底对不对。
毕竟在这里建造陵墓,还要考虑许多其他的问题。
比如土方平衡、河流改道、承重结构、淤泥沉积等等。
我不是专业学土建的,只能用自己能想到的方式,浅显的还原了一下,当年建造藩王墓的情形。
能运输淤泥的天井,肯定不止一个两个。
藩王既然敢把天井修的这么宽,就肯定不会害怕盗墓贼顺着天井爬进来。
这也意味着,藩王李璘有足够的信心,让所有擅闯禁地的盗墓贼,有来无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