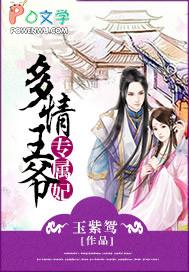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四合院:何大清刚想跑就被按住了 > 第145章 雨水(第2页)
第145章 雨水(第2页)
何雨柱心里咯噔一下。
他忽然有些明白了。
这种变化,或许不仅仅是“大姑娘了”那么简单。
这是一种成长过程中特有的迷惘和别扭,介于孩童与成人之间,想要挣脱什么,却又不知该去向何方;
渴望被理解,却又下意识地关闭心门。
他想起自己穿越前,似乎也经历过这么一段看什么都不太顺眼、觉得没人理解自己的时期。
那时候,他们通常把这叫做:
“叛逆期”。
五十年代的叛逆期,没有光怪陆离的网络世界,没有喧嚣震耳的流行音乐,更没有离家出走的惊世骇俗。
它更像是一道无声的壁垒,悄悄地、固执地,在原本亲密无间的兄妹之间竖了起来。
它藏在雨水拒绝新花布时那微微蹙起的眉头里;
藏在她宁愿对着窗外呆,也不愿再像小时候一样把心里话全都倒给哥哥听的沉默里;
藏在她对弟弟那句无心的羡慕里。
或许,她羡慕的是弟弟可以理所当然地享受所有人的关注和宠爱,而她却要开始面对成长的烦恼和来自周围更多的期望。
吃过晚饭,雨水一声不吭地回了自己西厢房,关上了门。
何雨柱没有像往常那样跟进去问问她的功课,他坐在书房里,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对待此时的雨水,或许不能再像对待那个需要他时时呵护、事事安排的小女孩了。
他需要一种新的方式。
第二天,何雨柱下班回来,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一趟新华书店。
他在里面转了近一个小时,出来时,手里多了一本包裹好的书。
晚上,他把书放在雨水房间的书桌上,什么也没说。
那是一本散文集,作者是几位当代的女作家,文字清丽,写的多是关于成长、关于理想、关于生活中细微的美好与烦恼。
何雨柱记得,雨水最近的作文里,开始出现一些模仿这类文风的句子。
雨水看到书时,愣了一下,拿起翻看了几页。
然后抬起头,看向站在门口的何雨柱,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却只化作一声低低的:
“谢谢哥哥。”
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虽然很快又恢复了平静,但何雨柱捕捉到了那一瞬间的亮光。
他没有追问她喜不喜欢,只是温和地说:“晚上看书别太晚,伤眼睛。”
“嗯。”雨水点了点头,这次没有立刻移开目光。
接下来的几天,雨水依旧没有变回那个叽叽喳喳的小女孩,但她关在房间里的时间似乎少了一些。
偶尔,她会拿着那本散文集,坐到院子的石榴树下看。
有时,何雨柱下班回来,会现书桌上放着一杯泡好的、温度刚好的茶。
她依然很少主动说起学校的事,但何雨柱不再像以前那样事无巨细地追问。
他开始学着在她沉默的时候,也保持一种有分寸的安静。
在她偶尔流露出一点想要交流的意愿时,认真地倾听,而不是急于给出建议或评判。
他知道,那扇悄悄关上的心门,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尊重去等待它重新打开,而不是强行去敲。
成长这场无声的春雨,终究需要她自己淋过,才能见到天边的虹。
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细细的,密密的,敲打着屋檐和窗棂。
何雨柱看着西厢房窗口透出的、温暖而安静的灯光,心里一片澄澈。
他或许无法完全理解十三岁少女的心事,他只能等,等雨水自己调节,人生特有的一段路,得她自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