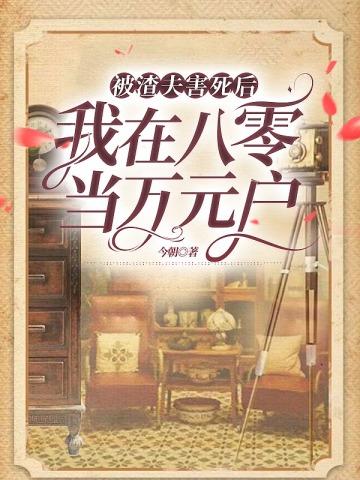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四合院:何大清刚想跑就被按住了 > 第140章 升官发财换老婆(第2页)
第140章 升官发财换老婆(第2页)
陈永贵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极淡的、几乎听不出的喟叹,“那孩子,我见了,面黄肌瘦,眼神怯得很。”
何雨柱能想象那画面。
一个耗尽青春伺候公婆、苦苦等待的女人,一个可能从未见过父亲或者早已记忆模糊的孩子。
面对的却是改名换姓、高升显贵的丈夫和父亲,以及冰冷的官僚推诿。
“清官难断家务事,这话不假。”
陈永贵话锋一转,目光变得锐利,“但这件事的影响,已经出了家务事的范畴。
我们收到一些零散反映,指向王秉国同志在其分管领域,可能存在利用职务之便,进行计划外物资调配的情况。
目前只是风闻,缺乏实证。
而他个人生活上的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与他工作上的问题交织在一起,
引更大的风波,影响很坏,也容易打草惊蛇。”
何雨柱立刻明白了。
陈永贵关注的,表面是生活作风,实则是潜在的经济问题。
物资调配,在这个计划经济的年代,是极其敏感且权力寻租空间巨大的领域。
官方在证据不足时不便直接调查一位厅级干部,尤其是在其个人生活问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的情况下。
需要有人从外围入手,找到突破口。
“张桂芳母子的遭遇,值得同情。王秉国同志如果确实存在问题,也不能姑息。”
陈永贵最后说道,目光落在何雨柱脸上,“你看,能不能想办法,从侧面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注意方式,掌握分寸。”
何雨柱迎着他的目光,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正好,我最近对这拍照有点兴趣,可以多出去走走,熟悉一下新相机。”
他没有把话说透,但陈永贵显然听懂了他话里的意思。
“嗯。”陈永贵满意地颔,“抓紧时间。”
“我尽力。”
正事谈完,陈永贵脸上的线条似乎柔和了些许,他随口问:“弄了台相机?”
“嗯,淘来的,个人兴趣。”何雨柱回答得自然。
陈永贵没再多问,又闲聊了两句,便告辞离开。
送走陈永贵,何雨柱回到书房,重新拿出那台徕卡相机。
冰凉的金属机身握在手中,带来一种沉甸甸的实感。
张桂芳,王秉国(原名王守成),厅级干部,计划外物资调配,无助的母子……
这些信息在他脑海中清晰起来。
他走到窗边,看着窗外尚未完全复苏的院落。
陈永贵给了他一个明确的任务,也给了他“灵活处理”的空间。
调查一位可能渎职贪腐的官员,符合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他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他有自己的考量与界限。
“王秉国……”他低声念着这个新名字,眼神平静,却带着一种行动的决心。
他打开书桌抽屉,开始检查里面的胶卷和一些可能用到的随身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