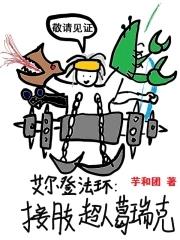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刚穿越,被千古一帝抢走半块饼 > 第236章 老友(第2页)
第236章 老友(第2页)
也很……温暖。
“唉,说起来,这身子骨,真是不行了。”樊哙一边说,一边捶着自己的膝盖,“一到阴雨天,这当年在垓下留下的老毛病,就跟针扎一样疼。”
韩信也点了点头:“我这后背也是。光阴不饶人啊。”
扶苏更是咳嗽了两声,拢了拢身上的裘衣:“人老了,不中用了。”
三个真正的“老人”,不约而同地出了对岁月无情的感慨。
他们说完,又下意识地一同将目光投向了那个从始至终都一言不的陈寻。
“先生,”扶苏看着陈寻那张,与几十年前,没有任何变化的脸,眼神复杂地轻声说道,“您看着我们,一个个从青年步入暮年。想必一定很孤独吧?”
樊哙也憨憨地附和道:“是啊!我们都快变成土了,先生你还跟当年在沛县时一个样!真他娘的……不公平!”
陈寻脸上的笑意,微微一滞。
他看着眼前这三位,他生命中最后也最重的故人。
那股被他强行压抑了数百年的、巨大的孤独感悄无声息地将他包裹。
他没有回答。
只是默默地,将碗中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韩信看出了他情绪的变化,立刻打了个哈哈,指着樊哙的鱼竿大笑道:“快看快看!鱼上钩了!樊胖子,你可抓稳了!别让鱼把你给拖下水去了!”
“滚你的!”樊哙笑骂着,手忙脚乱地开始收线。
沉重的气氛,再次被插科打诨所取代。
……
夕阳西下,又到了离别的时候。
樊哙要返回长安,扶苏也要返回彭城。
在府邸门口,四人再次告别。
“先生!帝师大人!韩信!”樊哙重重地拍了拍他们三人的肩膀,“别等下一个二十年了!有空都来长安!我请你们,去吃全城最好的狗肉!”
“一定。”
三人都笑着点头。
樊哙翻身上马,对着他们用力地挥了挥手。然后策马绝尘而去。
扶苏也登上了他那辆宽大的马车。
“老师,保重。”
“你也是。”
陈寻看着扶苏的马车,缓缓地消失在官道的尽头。
他知道下一次再见,不知,会是何年何月了。
“故人的时代……过去了啊,先生。”韩信站在他的身旁,轻声感慨。
陈寻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远处,韩信的儿子韩念,正和他的新婚妻子,一同向这边走来。
他缓缓地摇了摇头。
“没有过去。”
他看着韩信,笑了。
“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在延续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