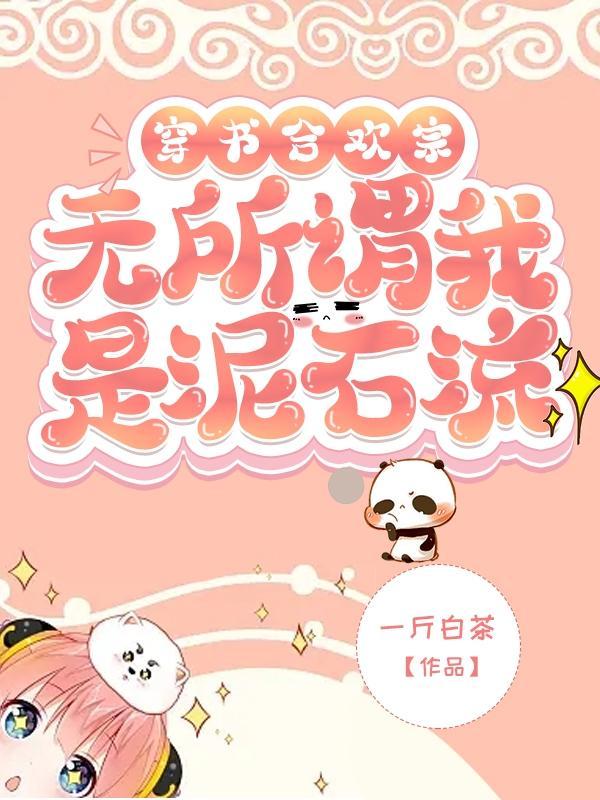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玉佩牵缘:真假千金沪上行 > 第0075章真假千金沪上行渔村(第3页)
第0075章真假千金沪上行渔村(第3页)
“算是吧。”莹莹轻声答。
“我叫陈朗,音专的学生。”男子自我介绍道,“你呢?”
“莫莹莹。”
简单的对话后,两人一时无言。陈朗看着她,忽然道:“莫同学,看你样子,不像那些……嗯,有钱人家的小姐。学音乐,不容易吧?”
这句话,无意间戳中了莹莹的心事。她低下头,没有回答。
陈朗却像是找到了知音,话多了起来:“这世道,有时候真不公平。有才华的,可能因为穷,连把像样的琴都买不起,更别说机会。而那些……哼。”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明显。
他扬了扬手里的琴弓:“我就不信,只有他们配搞艺术!音乐不该是金钱堆砌出来的!莫同学,你要是喜欢音乐,别轻易放弃。就算没有舞台,至少还能拉给自己听,唱给自己听!”
他的话,带着年轻人特有的愤慨和天真,却像一阵风,吹散了莹萦绕心头的部分阴霾。她抬起头,看着陈朗那双炽热的眼睛,轻轻点了点头。
“谢谢。”她说。
离开那条小街时,莹莹觉得脚步轻快了些。她摸了摸口袋里那本《义勇军进行曲》的册子,又想起陈朗的话。也许,路不止一条。也许,失去一个去巴黎的机会,并不意味着失去所有。
-
几天后,沈家派来的人再次到了渔村。这次来的是一位穿着体面长衫的账房先生,带着两个随从,态度比上次沈万昌更加客气周到。
账房先生先是再次表达了沈家的感激之情,然后呈上了一份礼单,上面罗列了更为具体的谢仪,除了之前的财物,还包括愿意资助阿贝去镇上甚至县里新式学堂读书的承诺。
“沈老爷说了,阿贝姑娘聪慧勇敢,屈居乡野实在是埋没了。若是姑娘愿意,沈家可以负责一切学杂费用,直至姑娘学业有成。”账房先生微笑着,看向坐在父母身后、低着头的阿贝。
莫老憨夫妇更是惶恐,连连道:“这怎么敢当……这……”
阿贝抬起头,看着账房先生,声音不大却清晰:“谢谢沈老爷好意。只是……我习惯了渔村的生活,还要帮着爹娘干活。读书……就不用了。”
账房先生有些意外,劝道:“姑娘,机会难得。读了书,明事理,将来或许能有更好的出路,不必再如此辛苦。”
阿贝沉默着,摇了摇头。她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抗拒。沈家的馈赠太重,重得让她不安。她救人不图这些,若接受了,仿佛那单纯的举动就变了味道。而且,离开渔村,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她不敢想。
账房先生见她态度坚决,也不好再强求,又寒暄几句,留下礼单和一些实用的礼物(如成药、布匹),便告辞了。
送走沈家的人,莫老憨看着女儿,叹了口气:“阿贝,沈家是真心实意,你……”
“爹,我知道。”阿贝打断他,“但我们不能靠着别人的感激过一辈子。这些钱和东西,我们省着用,或者……以后有机会,帮衬更需要的人也好。我自己有手有脚,能养活自己。”
她走到窗边,望着外面熟悉的河流和船只。沈家的出现,像一颗投入水面的石子,涟漪过后,水面似乎恢复了平静,但水底的东西,却被搅动了。她下意识地又摸了摸颈间的半块玉佩。这玉佩,和沈家的厚礼一样,都指向一个她未知的、模糊的过去和未来。
-
莹莹再次去了那个小公园。这次,那几个学生还在,募捐箱前的人似乎多了一些。她看到陈朗也在,他正和一个工人打扮的男子说着什么,神情激动。
莹莹没有立刻上前,她站在不远处看着。陈朗看到了她,朝她点了点头。
募捐活动间歇,陈朗走过来,额上带着汗珠。“莫同学,你来了。”
“嗯。”莹莹应了一声,犹豫了一下,问道,“你们……经常做这些吗?”
“能做的有限。”陈朗抹了把汗,“募捐、宣传、唤醒民众。国家到了这个地步,总不能人人都做缩头乌龟。”他看了看莹莹,“我看你上次也捐了钱,是有心人。”
莹莹低下头:“只是……一点心意。”
“心意无价。”陈朗郑重道,随即他又兴奋起来,“对了,我们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合唱团,唱一些进步歌曲,鼓舞士气。就在光华大学附近活动,你要不要来看看?”
莹莹心念微动。唱歌……那是她真正喜欢,并且能让她暂时忘记烦恼的事情。
“我……可以吗?”
“当然!”陈朗眼睛一亮,“欢迎任何有志青年!”
第一次去那个所谓的“合唱团”,是在一个大学的废弃仓库里。条件简陋,只有一架走音的旧钢琴,十几个男女学生,穿着朴素,但眼神都和陈朗一样,带着光。
他们唱的不是学校里教的西洋咏叹调或风花雪月的流行曲,而是《毕业歌》、《大路歌》,还有那《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或许不够专业,甚至有些参差不齐,但那蓬勃的力量,那自肺腑的激情,却深深震撼了莹莹。
她站在角落里,听着,看着,胸口有什么东西在涌动。
“来,莫同学,一起唱!”陈朗向她招手。
莹莹有些怯场,但在那些热情目光的鼓励下,她慢慢走上前,跟着旋律,轻声哼唱起来。
起初声音很小,渐渐地,她放开了嗓子。清越的嗓音融入集体的和声,仿佛水滴汇入河流。她唱著「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唱著「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唱着唱着,眼眶竟有些湿润。在这里,没有人关心她是不是落魄千金,没有人用家世来衡量她。在这里,音乐不再是攀附风雅的工具,而是呐喊,是武器,是凝聚人心的力量。
排练结束,陈朗走到她身边,由衷赞道:“莫同学,你唱得真好!很有感情!”
莹莹脸上泛起一丝红晕,这是失去音乐学校的推荐名额后,第一次有人如此真诚地肯定她的歌声。
“是这些歌……写得好。”她轻声说。
“歌好,也要唱的人用心。”陈朗看着她,眼神明亮,“下周末我们有一场小型的公开演出,就在大学礼堂,你来担任《渔光曲》的领唱,怎么样?”
莹莹的心猛地一跳。领唱?公开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