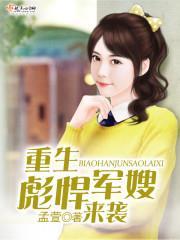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梦幻旅游者 > 第296章 香串风波(第3页)
第296章 香串风波(第3页)
宝钗叹道:“果然如此。我早听说忠顺王府一直在找北静王的错处。那香串若是处理不当,恐怕会酿成大祸。”
二人相视一眼,心中都明白其中利害。宝钗忽然道:“那日宝玉要将香串赠你,你拒绝得好。”
黛玉微微一笑:“姐姐不也提醒得及时?”
宝钗打量黛玉片刻,轻声道:“林妹妹,你我一向不算亲近,但我心里是佩服你的。这府中多是糊涂人,难得有你我这等明白人。”
黛玉闻言,对宝钗的看法也有所改观。原来她并非一味圆滑世故,而是深明大义,顾全大局。
却说宝玉被叫到王夫人房中,原来是薛姨妈来了,带来些时新果品。宝玉陪着说了一会话,薛姨妈忽然问道:“听说前日北静王赠了你一串香串?”
宝玉心中暗惊,怎么连薛姨妈都知道了?只得答道:“是,不过我已好生收起来了。”
薛姨妈点头道:“收起来好。御赐之物,非同小可。听说忠顺王府的人昨日来过了?”
王夫人接口道:“正是呢,莫名其妙地问起香串的事,吓得我心跳不已。幸亏宝玉没有糊涂到处炫耀。”
薛姨妈道:“姐姐不知道,如今朝中局势复杂。忠顺王府与北静王明争暗斗,我们这些人家,稍有不慎就会卷进去。”说着压低声音,“听说皇上对北静王与老臣世家交往过密很是不满呢。”
王夫人叹道:“这些朝堂大事,我们内宅妇人哪里懂得?只是苦了孩子们,连收份礼物都提心吊胆的。”
宝玉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这才明白黛玉那日为何反应如此激烈。原来这小小一串念珠,竟牵扯着如此复杂的朝堂争斗。
晚间歇息时,宝玉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黛玉那日的态度,愈觉得她非同一般女子。她看似孤高自许,实则深明大义;看似敏感多疑,实则洞察世事。
次日,宝玉特意往潇湘馆去。见黛玉正在抚琴,便静静站在一旁聆听。琴声淙淙,如流水般清澈,却又带着几分忧思。
一曲终了,黛玉抬头见是宝玉,微微一笑:“怎么不声不响地站着?”
宝玉道:“听妹妹抚琴,如聆仙乐,不忍打扰。”顿了顿,又道:“我是来谢妹妹的。”
黛玉不解:“谢我什么?”
“谢那日妹妹拒收香串。”宝玉诚恳道,“我原以为妹妹是使小性儿,如今才明白妹妹是深谋远虑。若不是妹妹,恐怕我已经惹出大祸了。”
黛玉轻抚琴弦,淡淡道:“你如今明白了就好。我们身处贾府这般人家,一言一行都有人盯着,不得不谨慎。”
宝玉叹道:“只是这般活着,也太累了。连送个礼物都要思前想后。”
黛玉抬头看他,眼中闪过一丝怜悯:“你呀,就是太过天真。殊不知这世间多少祸事,都因一时不慎而起。”她想起父亲林如海生前教诲,轻声道:“我父亲常说:‘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如今想来,真是至理名言。”
宝玉闻言,对黛玉更是敬佩。原来她不止才华横溢,更得父亲真传,深谙世情人心。
却说那串鹡鸰香念珠,宝玉本已收在箱底,不再取出。不料一日贾母忽然问起:“听说北静王赠了你一串香串?取来我瞧瞧。”
宝玉只得取来。贾母仔细看后,叹道:“果真是好东西。只是。。。”她沉吟片刻,“御赐之物,北静王转赠于你,实在不妥。你还是寻个机会,委婉归还才是。”
宝玉为难道:“这。。。如何归还?岂不是驳了北静王的面子?”
贾母道:“总比留下祸根强。你就说御赐之物,不敢轻易收受,故而奉还。”
宝玉只得应下。
几日后,北静王府设宴,邀请贾府众人。宝玉趁机求见北静王,委婉表示要归还香串。
北静王闻言大笑:“世侄何必如此拘礼?本王赠你,你收下便是。”
宝玉恭敬道:“王爷厚爱,晚辈感激不尽。只是这是圣上亲赐之物,晚辈年轻识浅,恐保管不周,有负圣恩。还请王爷收回。”
北静王打量宝玉片刻,忽然问:“可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宝玉不敢隐瞒,只得将忠顺王府长史官来访之事略说一二。
北静王听后,面色微沉,随即笑道:“难得世侄如此谨慎。既然如此,本王就收回吧。免得给你招来麻烦。”
宝玉这才松了口气,心中对黛玉的远见更是佩服不已。
宴席间,宝玉偶遇北静王府的一位老嬷嬷。老嬷嬷见宝玉面生,问起来历,得知是贾府公子,便多说了几句:“王爷最近得了一幅好画,说是令尊推荐的。王爷与贾公真是投缘。”
宝玉谦虚几句。老嬷嬷又道:“王爷最爱才,听说贵府有位林姑娘,才华横溢,不知何时有缘得见?”
宝玉心中一惊,忙道:“表妹深居简出,怕是不便见客。”
老嬷嬷笑道:“老身多嘴了。只是听说林姑娘的父亲是前科探花,王爷最敬重读书人,故而有此一问。”
宝玉回去后,将此事悄悄告知黛玉。黛玉听后,沉吟道:“北静王为何突然问起我?莫非是那香串的事传出去了?”
宝玉道:“不至于吧?你不是没收吗?”
黛玉摇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恐怕那日你欲赠我香串之事,被人知道了。”
宝玉懊恼道:“定是我那日太过张扬,让人看见了。”
黛玉叹道:“事已至此,只好更加谨慎了。日后北静王府若再有人问起我,你一概推说不知便是。”
果然,过了几日,北静王府又派人来请贾府女眷过府赏花。请柬上特意提到“久闻林姑娘才名,盼得一见”。
贾母见状,心下明了,对王夫人道:“北静王府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王夫人担忧道:“这可如何是好?黛玉那孩子心气高,恐怕不愿攀附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