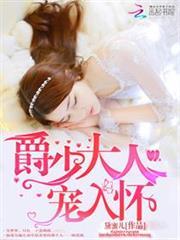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嫡明 > 第406章 江宁侯陛下召见(第3页)
第406章 江宁侯陛下召见(第3页)
而且,圣旨中说“卿等”,而不是说“卿”,对经略相公本人的功劳提都不提,这是故意淡化经略的抗倭大功。
皇上这么做是不是过了?即便猜忌经略相公,也不用这么着急啊。
难道朝中还出了什么事?
一时间,别说是熊廷弼、毛文龙、曹文诏等将领,就是李如松、麻贵等人,也为朱寅感到不平。
冯梦龙、孙承宗、高攀龙这三个幕僚,都腹诽皇帝所作所为不厚道。
相反的是,高丽君臣却是心中舒爽,大有扬眉吐气之感。
原来,明国皇帝撤换了朱寅,改派这个宋相公为新的经略。
这道圣旨一下,朱寅就无权插手高丽大事了,只能灰溜溜的滚回去。
哈哈哈,好!太好了!
此时此刻,高丽君臣满心都是朱寅被撤的欣喜,浑然忘记了是朱寅率军数次大败倭寇,这才解高丽于倒悬。
他们只记得朱寅的“专横跋扈”、“颐指气使”、“油盐不进”,只记得朱寅对他们的“羞辱”、“欺压”。
至于朱寅对高丽的恩德,他们下意识的过滤掉了。
他们眼下只想讨新经略欢心。怎么巴结新经略呢?最好的办法当然是冷落前经略,巴结新经略了。
“臣领旨,谢恩!”朱寅的神色很是平静。
宋应昌将圣旨交到朱寅手中,扶起朱寅,有些愧疚的说道:“稚虎贤弟,我实在不愿来接替你啊,可也只能遵旨而来…”
他和朱寅关系不错,真不想当这个新的经略使。
仗都打完了,根本没有必要换帅。陛下对朱寅,实在是刻薄了。
宋应昌还知道,陛下已经决定贬谪朱寅为知县。他很为朱寅感到不平。
“思文兄来,总比其他人来好的太多。”朱寅无所谓的笑道,“接下来的高丽大事,就拜托思文兄了。”
宋应昌叹息一声,苦笑道:“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来高丽是摘桃子的。公道自在人心,稚虎贤弟不在意,不代表天下人心服啊。”
高丽王不知道宋应昌和朱寅私交很好,还以为两人只是逢场作戏,自作聪明的认为宋应昌说的是反话,立刻上前说道:
“经略相公远道而来,舟车劳顿,还请入席座!”
柳成龙等一群高丽大臣,也争先恐后的口称“经略相公”,请宋应昌位上座。
当着朱寅的面,这么快就称呼宋应昌为经略,还请宋应昌入席座,实在是太过势利了。
因为宋应昌入座,意味着之前坐在座的朱寅要挪位置!
宋应昌不露声色的看了高丽王一眼,淡然说道:“不必了,本官随便坐吧,殿下不用麻烦。”
对于这个高丽王的肺腑,他已经心知肚明。
高丽君臣也不敢违拗,请宋应昌坐下来,又经略长、经略短,好一番奉承。
“经略相公到此,高丽如赤子得见父母,自从无忧矣。”
“我等盼经略相公,如久旱盼甘霖…”
“经略相公再上,我等敬相公一杯…”
高丽君臣谀词如潮,对宋应昌十分热情。而对朱寅,却是理都不理,只当作空气一般。而且恭维宋应昌的话语之中,还暗暗影射朱寅对高丽不好。
真就是…人未走,茶已凉。
这种见风使舵的炎凉之态,让李如松、努尔哈赤等人都难以接受。
高丽君臣自作聪明,以为新经略和朱寅肯定不对付,他们故意冷落朱寅,企图换取新经略的好感。殊不知不但没能讨好新经略,反而引起新经略的鄙视和反感。
但宋应昌何等样人?他当然不会当场作,只是对朱寅使个眼色,彼此心中有数而已。
他自然能看出,稚虎对这些高丽君臣的势利毫不在意,完全不萦心怀。
高丽君臣一变卦,高丽贵女们对宁清尘也不再巴结了。
她们都懒得再和宁清尘说话,一个个变得冷漠起来。
这番作态,宁清尘也毫不在意。横竖棒子就是这副肤浅可笑的小丑德性,后世也是如此。
不这样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