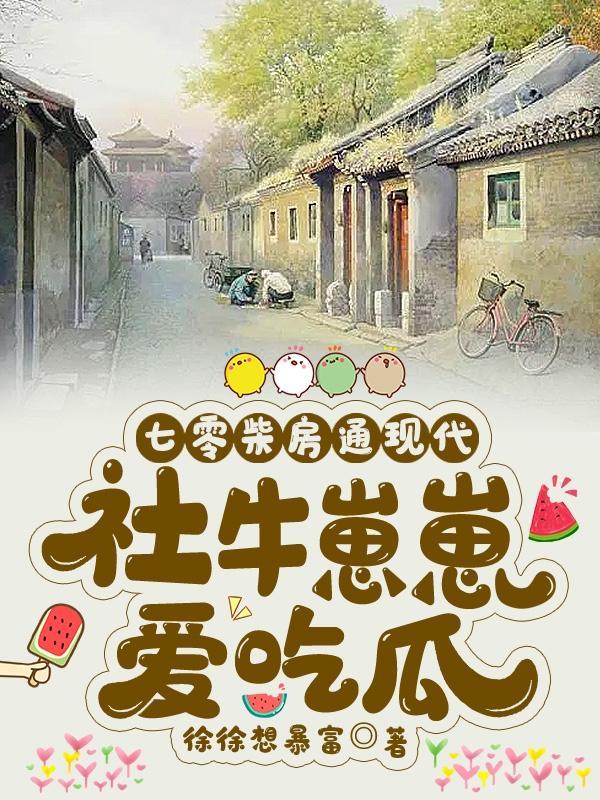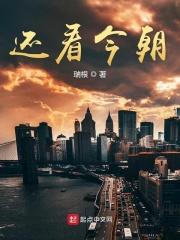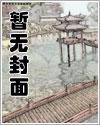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生个孩子姓易,把一大爷钓成翘嘴 > 第14章 四合院富婆金手指到账 超市空间(第1页)
第14章 四合院富婆金手指到账 超市空间(第1页)
认门的喧嚣散去,夜色已深。
韦东毅跟着易中海回到易家时,一大妈正坐在灯下缝补着什么。
见他们进来,她放下针线,起身给每人倒了一杯热腾腾的茉莉花茶,茶香氤氲,驱散了夜间的微寒。
“东毅啊,”一大妈将茶杯推到韦东毅面前,语气自然又带着不容置疑的关切,“你原先带来的那条床单,我看边上都磨毛了,还破了个小口子,已经给你换了条全新的铺上了。那条旧的,明儿妈给你缝补好,洗得干干净净的再给你收着。”
“谢谢妈。”韦东毅捧着温热的茶杯,暖意从指尖蔓延到心底。
这句“妈”叫得越来越顺口。
一大妈嗔怪地拍了他胳膊一下:“一家人,谢来谢去生分了不是?”
易中海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看着韦东毅,提出了思量已久的建议:“东毅,还有个事。你看,你一个人开火做饭,锅碗瓢盆置办齐了也麻烦,生火做饭还耽误时间。不如就跟老太太一样,都在我和你妈这儿搭伙吃?反正你妈也不上班,多添双筷子的事儿!”
韦东毅略一沉吟。
自己开火确实琐碎,尤其是刚安顿下来。
他爽快点头:“行!那我每月交十块钱伙食费,不能让爸妈贴补。”
“嘿!你这孩子!”易中海立刻板起脸,佯装不悦,“提什么钱?把粮本交给你妈就行!你那点工资,自己攒着,往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吃饭能吃穷你爸我?等你往后娶了媳妇,想自个儿开小灶了,再搬出去也不迟!”
他语气豪迈,底气十足。
八级钳工九十九块五的月薪,在这年头,养四个人吃饭,绰绰有余。
韦东毅看着易中海不容置疑的神色,又看看一大妈含笑点头的样子,心中了然。
既然认下了这门干亲,也存了为他们养老的心,再算得锱铢必较,反倒显得生疏了。
他笑了笑,不再坚持:“好,都听爸的。”
一旁的老太太自始至终没插话,布满皱纹的脸上却一直挂着安详满足的笑意。
人活到她这把年纪,黄土都埋到了下巴颏,早已看淡了浮世纷扰。
她唯一放不下的,就是这失而复得的亲孙儿。
如今亲眼见孙儿认下易家这门干亲,有了依靠,有了“父母”的牵挂,她悬着的心,才算真正落回了肚子里。
老太太看人极准,在她心里,这偌大的四合院,真正能称得上“好人”二字的,除了傻柱那憨直的,也就易中海这两口子了。
当然,这份“好”,也需要孙儿用真心去维系,去解决他们无后的隐忧。
一家“四口”又闲话了一阵家常,夜色渐浓。
韦东毅起身,稳稳地背起老太太,送她回后院那间熟悉的后罩房。
老太太伏在孙子宽厚的背上,枯瘦的手臂环着他的脖颈,满是依恋。
进了屋,她拉着韦东毅的手,在炕沿坐下,浑浊的眼里是化不开的慈爱和不舍。
“乖孙儿,”老太太声音带着点神秘,指了指炕沿底下,“去,把床底下那个大木箱子拖出来。奶奶有东西要交给你。”
韦东毅依言弯腰,手探入床底,摸到一个沉重的实木箱子边缘。
他稍一用力,将其拖拽出来。
箱子入手沉甸甸的,怕是有好几十斤。
箱体是深色的老榆木,四角包着黄铜,挂着一把厚重的“雄狮”牌铁锁,透着岁月的沧桑。
老太太颤巍巍地从贴身小袄里摸出一枚磨得锃亮的铜钥匙递过来:“打开它。”
钥匙插入锁孔,轻轻一拧,“咔哒”一声脆响,铁锁应声弹开。
韦东毅掀开厚重的箱盖,一股淡淡的樟脑和旧木混合的气味飘散出来。
映入眼帘的,先是一面叠得整整齐齐的红绸布。
他小心地将其取出,展开——赫然是一面锦旗!
鲜红的绸面上,八个遒劲有力的金色大字:人民功臣,无上光荣!
锦旗之下,静静躺着一个同样红漆的木匣。
老太太用眼神示意。
韦东毅轻轻放下锦旗,屏住呼吸,打开了红匣。
匣内,红丝绒衬底上,一枚铜质的圆形勋章静静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