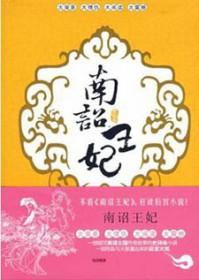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穿越到古代穷的只剩下一把砍柴刀 > 第303章 升龙城(第1页)
第303章 升龙城(第1页)
飞鱼卫的脚步声踏碎南疆的晨雾,代州军的战旗在风里猎猎作响,可当升龙城的轮廓真正撞进眼帘时,连最悍勇的士兵都忍不住倒抽一口凉气。
那不是之前踏破的任何一座小城!青黑色的巨石城墙像从地底生出来的山,直插云霄,墙顶的雉堞密密麻麻,隐约能看见寒光闪烁的箭尖。
护城河宽得能跑三艘战船,深绿色的河水泛着冷意,连风刮过都带着铁锈般的杀气——这就是南越国都,一座用石头和恐惧堆起来的巨兽!
自飞鱼卫授旗以来多为水战,攻城之战少之又少,想要攻破此城付出代价必不会少……
“报!代州军已至城下!城外三座营寨的兵力,全、全撤回来了!”
皇宫大殿里,内侍的尖叫像被掐住脖子的公鸡。
伪王黎殇猛地从龙椅上滑下来,锦袍下摆蹭满了龙纹地毯的绒毛,他抖得像筛糠,手指死死抠着柱子:“怎、怎么会这么快?那些象兵呢?阮将军不是说……”
话没说完,黎嵩的眼神就像冰锥扎了过来。
这位南越实际掌权者脸色铁青,指节攥得白:“慌什么!撤回来正好!升龙城的皇城才是真正的堡垒,那些土城挡不住,不代表这巨石墙也挡不住!”
大将军阮中元跨步上前,铠甲碰撞声在死寂的大殿里格外刺耳:“殿下放心,臣已传令,所有弓箭手、守城兵卒全上城,滚木礌石堆了三层,连民间的火油都搜空了——他们想攻进来,得先踏过成百上千具尸体!”
黎殇这才勉强扶稳瘫坐在龙椅上,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
他没看见,黎嵩和阮中元对视时,眼底藏着的不是底气,是赌徒般的疯狂——他们赌的,是代州军的补给,是那支传闻中能打硬仗的飞鱼卫,撑不了多久!
而此刻,升龙城下的飞鱼卫大营里,气氛沉得能拧出水。
赵天啸站在沙盘前,手指按在升龙城的模型上,指腹磨得生疼。
沙盘旁的木牌上,一道红痕刺眼——飞鱼卫,一千二百人。
谁能想到,跟象骑兵那场恶战,竟折损了近八百兄弟!
他想起那些被象蹄踏碎的盔甲,想起弟兄们临死前抱着掌心雷与象兵同归于尽时还在喊“为了主公,代州必胜!”,喉咙就像被塞进了烧红的铁块。
轰!
实心铁弹狠狠砸在升龙皇城的巨墙上,碎石飞溅,却只留下一个泛白的凹坑。
墙头箭垛后的南越守军出放肆的嘲弄,箭雨更加密集地泼洒下来,逼得飞鱼卫进攻的队伍再次狼狈后撤。
“将军!不行啊!这墙他娘的根本啃不动!”一个满脸血污的校尉冲到赵天啸面前,声音嘶哑,“弟兄们又折了十几个!”
赵天啸站在临时垒起的土坡上,面无表情。
寒风吹起他染血的战袍,露出下面破损的甲叶。他握着刀柄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根根白。
眼前这座皇城,像一头匍匐在大地上的黑色巨兽,冰冷、坚固、傲慢。
墙高过五丈,全是用南方特有的厚重青石砌成,接缝处灌了米浆铁汁,坚固无比。
护城河宽得像是人工开凿的湖泊,浑浊的水面下不知藏着多少尖桩。
城墙上,黎殇和阮中元的旗帜嚣张地飘扬。弓箭手、滚木、擂石、还有那一锅锅烧得滚沸、冒着刺鼻气味的火油……防守的密集程度令人窒息。他们打定了主意,当缩头乌龟,就是要活活耗死你!
“火药还有多少?”赵天啸的声音沙哑,几乎被风扯碎。
跟在他身后的军需官身子一颤,低声道:“回将军,重炮用的射药只剩不到三十份,开花弹……只有十五颗了。火铳用的子药也严重不足,最多……最多再支撑两次像样的进攻。”
绝望的情绪像冰冷的毒蛇,缠绕在每个飞鱼卫军官的心头。
二千飞鱼卫,一路从尸山血海里杀过来,干翻了象骑兵,踏平了无数寨堡,终于兵临这南越国都之下,却要被这龟壳一样的城池活活憋死!
打,打不进去。
![[综漫+扭蛋同人] 潜行吧,姐姐大人](/img/37818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