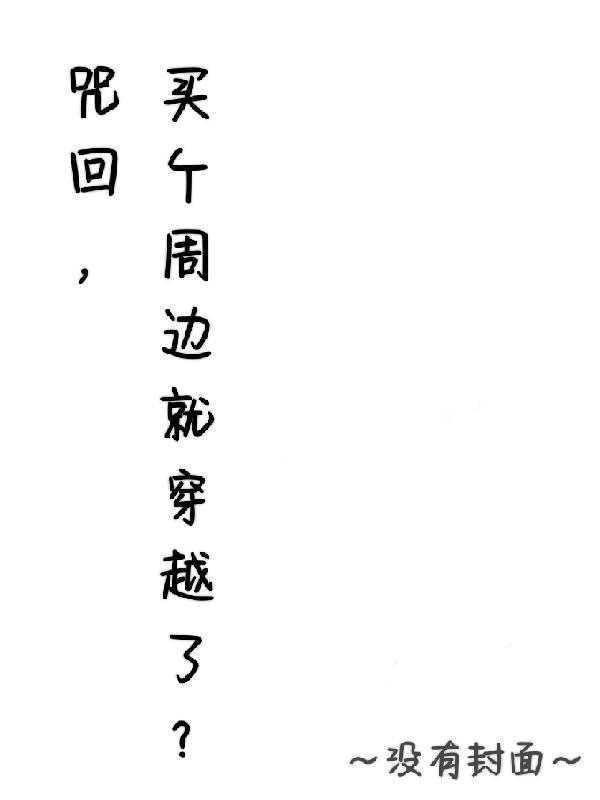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你的荣耀我的狙 > 第45章 外婆病逝(第2页)
第45章 外婆病逝(第2页)
这样的原因…只可能是,外婆的病更重了,或者…
出事了。
郁江澜心一沉,强烈的不安驱使他给舅妈打去电话,没有人接。
家里,也没人接。
郁江澜看了凌季北一眼,犹豫了片刻,开口道:“凌凌,我可能要回滨州一趟。”
—
第二天一早的飞机。
郁江澜候机的时候,忽然有人从后面跑上来,去蒙他眼睛。
“澜哥!”
熟悉的一声唤。
郁江澜不由得皱起眉,握住那人的手缓缓拉下来,转过身看着冲他笑的小孩儿,又冷又严肃:“你干什么,谁让你出院的?”
“别担心,我没事儿了,我问过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凌季北展颜一笑,掏出同班机票在郁江澜眼前扬了扬,顺势坐在后者的行李箱上,掷地有声道:“滨州么,我陪你去。”
郁江澜微怔,短暂的温情化作雾气从寂寥的眼底涌起,他偏过头,低声道了句:“傻瓜。”
他说着张开双臂,温柔地把小孩儿从行李箱上抱了下来:“别摔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明明只比凌季北大三岁,却始终觉得操着老父亲的心,总觉得他不管多大,依旧是个小孩儿。
—
飞机从北京飞往济南,再从济南坐两个半小时的汽车回滨州。
路上郁江澜打了无数个电话,都没人接听。
凌季北握着他的手,不停地安慰:“没事的澜哥,可能手机丢了呢,或者临时有事,都是大人了,别瞎想了,一定没事的。”
他说再多都无济于事,郁江澜浑身发抖,不好的预感一波一波袭来,心悸不断,难受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苍白无力地点头。
回到家,果不其然,没有人。
家里乱七八糟,沙发前的地上摆满了空酒瓶,花生皮到处都是,茶几上的烟灰缸里,数不胜数的烟头已经被水泡得发黄,散发出一股恶心的味道。
外婆的房间开着门,床上的被子凌乱着,竟然没有叠。
记忆里,就算那个老人病了,但是她叠被子的习惯也是不会变的,总是能像雕琢一件艺术品一样,工工整整地叠成一个漂亮的小方块,再把床单铺展得看不见一条褶皱。
怎么了,究竟是发生什么了。
郁江澜心里乱糟糟的,虽然几乎可以确定家里没人,他还是跌跌撞撞地把房子上上下下都查看了一遍。
最后从楼下物业得知,三天前,六楼一个老太太突发脑溢血,被救护车拉走了。
郁江澜喉头一紧,他张了张口,一时间竟然说不出话,嗓子眼又痛又干。
凌季北问物业:“请问您知道是送去哪家医院了吗?”
物业:“应该是人民医院吧,离得最近,也是这片儿最好的,一般这小区有啥病人都是去这医院。”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凌季北说着拿出手机叫滴滴,打车去人民医院。
郁江澜急疯了,上了车后一刻不停地打电话,给谁打电话,谁都不接。
他手脚冰凉,僵硬得几乎不受控制。
凌季北一直握着郁江澜的手,感受着那种来源于五脏六腑的颤抖,一刻不停。
“澜哥别害怕,没事的,”凌季北去揉搓着他那不通血脉,仿佛冰块一样冷的指尖,强颜欢笑:“可能不是你外婆呢,只是巧合也住在六楼呢。而且就算是,脑溢血也能治好的,我爸有个朋友就得了脑溢血了,当时还特别严重呢,后来也治好了,恢复得特别好!”
郁江澜闭着眼睛靠在车座上,喉结艰难地往下滑了滑,很压抑地呼吸着,他拇指抬了抬,在对方的虎口处摩挲了一下。
温存流连,尽在不言之中。
到了医院,郁江澜报出外婆的身份信息,查询对应的病房。
得到的结果是:病人已经于三天前宣告抢救无效病逝,今天清晨刚刚拉去殡仪馆,节哀。
!!!
病逝。殡仪馆。三天前。
这些字眼在郁江澜脑子里连环炸开,无疑是重叠的晴天霹雳。
他腿发软,愣了足足十几秒,再开口时,嗓子忽然就哑了,问说:“会不会是…搞错了?”
“能不能…再帮我看看…”
“没错的,就是邓秀芬嘛,你看,七十八岁,女,身份证号…”
…
那天原本真的是个晴天,可天不知从何时起,忽然就黑了大片。
郁江澜到底还是没能见到外婆最后一眼。
他火急火燎感到殡仪馆,正好撞见沈强和舅妈,两人在一众亲朋的簇拥慰问下走出来。
不用想都知道,肯定是借着这个机会收了不少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