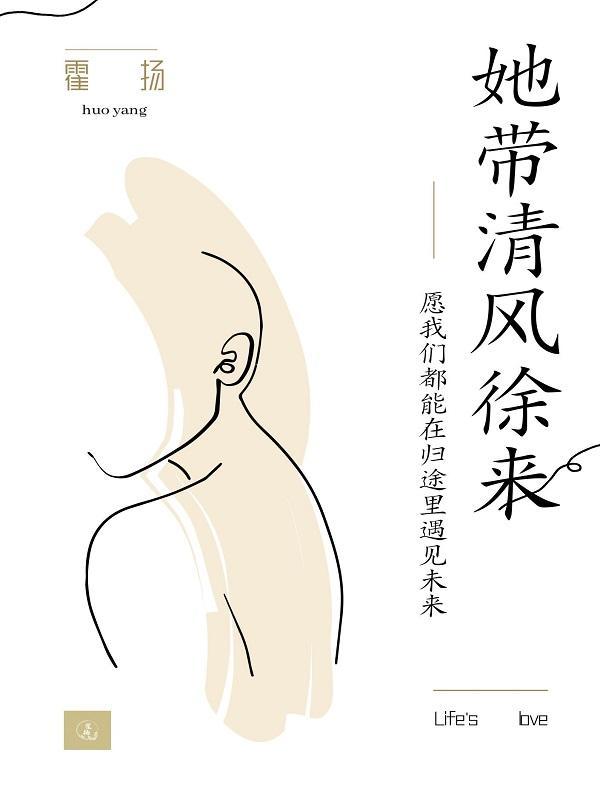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诡异的公交车 > 第266章 遗忘之桥(第1页)
第266章 遗忘之桥(第1页)
我下了车。雨终于停了,空气里却还悬着湿冷的水汽,像是从地底渗出的阴气,缠在脚踝上不肯散去。石桥横在眼前,灰白的石板被岁月磨得光滑,边缘爬满青苔,像是一道横亘在生与死之间的界碑。桥下是条河,黑得不似水流,倒像凝固的墨汁,沉甸甸地压在地脉之上。天上明明有月,可水面却照不出一丝光亮,仿佛那轮清辉也惧怕这河底的深渊,不敢垂落。
身后,1o7路公交车缓缓启动,车灯在浓雾中晕开两团昏黄的光晕,像一双疲惫的眼睛。它没有鸣笛,也没有引擎的轰鸣,只是悄无声息地退入雾中,仿佛从未存在过。我望着它消失的方向,心头忽然一空,像是被抽走了一部分记忆——可我分明记得自己是谁,记得上车,记得那一路颠簸,记得黑雨衣女人低垂的头,记得校服男孩手中那本写满名字的作业本。
我转身,桥头立着一块石碑,通体漆黑,像是用某种不知名的矿石雕成。碑面粗糙,却清晰刻着两行字:
“遗忘之桥:渡者留名,醒者归途。”
字迹歪斜,像是被人用指甲生生抠出来的,带着某种执念的痛楚。我摸出随身携带的钢笔——那是母亲留下的遗物,笔身刻着“勿忘”二字——在碑上写下“林晚”两个字。笔尖触石的瞬间,碑面忽然微微震颤,仿佛活物般吸了一口气。字迹刚成,石碑竟泛起一层暗红的微光,烫得我指尖一缩。一股寒意顺着笔杆窜上手臂,直抵心口。我猛地后退一步,却感觉脑中某段记忆正在被抽离——不是忘记,而是被“收走”,像是这碑在吞噬我的过往。
我闭了闭眼,强迫自己冷静。可就在我睁眼的刹那,桥下传来一声极轻的呼救,像是从水底深处浮上来的叹息。
“救……我……”
我蹲下身,探头看向桥下。那漆黑的河面依旧死寂,可就在我凝视的瞬间,水面忽然泛起涟漪,一张脸浮了上来——是司机,那张总是沉默的脸,此刻扭曲着,眼眶空洞,嘴唇开合,却不出声音。紧接着,第二张脸浮现——黑雨衣女人,她的雨帽掀开,露出苍白的脸,丝如水草般漂浮。然后是校服男孩,他的校牌上写着“陈默”,眼睛睁得极大,像是在无声尖叫。草帽父亲抱着一个空荡荡的婴儿背带,红裙小芸的辫子散了,手里还攥着半截糖葫芦……
一张又一张,密密麻麻,像是河底埋葬了整辆公交车的乘客。他们都在水下,仰面朝上,嘴唇不断开合,却无声音传出。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我身上,带着哀求,带着怨恨,带着某种无法言说的执念。
“你们……不能走?”我颤抖着问,声音在桥上回荡,却无人回应。
就在这时,石碑突然出一声低沉的嗡鸣。我回头,只见碑文悄然变化,旧字褪去,新字浮现:
“唯有全部‘反应’,方能解脱。”
我浑身一震,像是被雷击中。反应?什么反应?我猛然想起上车时,司机曾说:“有人看见,有人装睡,有人哭,有人笑——可只有‘反应’,才能留下痕迹。”当时我不懂,如今才明白:那不是情绪,而是“觉醒”——是意识到自己已不在人间,是承认自己早已死去。
可车上那么多人,大多低头看手机,或闭目假寐,仿佛一切正常。他们不愿醒,不敢醒。而我,是唯一一个在终点站下车的人,是唯一一个写下名字的人,是唯一一个“反应”了的人。
可这还不够。
碑文说“全部”,意味着我一个人的觉醒,无法渡桥。若我不唤醒他们,他们将永远沉在河底,成为这桥下的浮尸,而我也无法真正踏上归途。
我猛地转身,想冲回雾中追那辆1o7路,可桥身忽然剧烈震动,石板缝隙中渗出黑色的水,腥臭扑鼻。我低头一看,那些浮在水面的脸竟开始缓缓下沉,像是被某种力量拖拽回深渊。他们的嘴张得更大,手指向上伸着,仿佛在做最后的挽留。
“等等!”我扑到桥边,伸手欲抓,却只捞起一捧冰冷的黑水。
就在这时,碑文再次变化,字迹如血般浮现:
“归途已启,逆流者亡。”
我僵在原地。原来这桥,只许进,不许出。一旦写下名字,便不能再回头。若我执意返回,或许连自己也会沉入河底,成为那无数张脸中的一张。
可我怎能独自离去?
我闭上眼,脑海中闪过车上的一幕幕:黑雨衣女人在第七站突然抬头,看了我一眼;校服男孩在过桥时低声念着“他们都不记得了”;草帽父亲在终点站前突然抱紧背带,喃喃“她还在等我”……他们并非全然麻木,他们心中有裂痕,有微光,只是被恐惧压住了。
或许,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引子”。
我咬破指尖,将血抹在碑上,轻声说:“若我不能回头,那便让桥记住他们。”
血渗入石缝,碑面忽然剧烈震颤,一道裂痕自上而下崩开。刹那间,桥下黑水翻涌,那些沉下去的脸又缓缓浮起,这一次,他们不再无声呐喊,而是齐齐望向我,眼中竟有了一丝清明。
我举起笔,在碑侧空白处,一笔一划写下:
“陈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