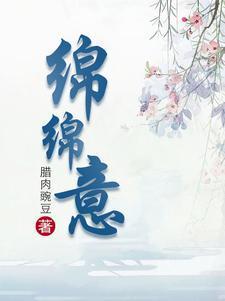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清宫秘史十二章 > 第302章 溥仪大婚(第1页)
第302章 溥仪大婚(第1页)
转眼五年过去了,1922年,这一年溥仪17岁。
按照大清礼仪,他到了婚配年龄。
这年深秋,紫禁城养心殿暖阁里,帝师陈宝琛扶着紫檀木椅扶手,对旁边的人,语调激动说道,
“皇上大婚,非止一姓之喜,实乃国本所系。”他的花白胡须因激动而颤抖。
我与苏龛(郑孝胥字)合计,这婚礼须照同治、光绪旧制办,让京中百姓看看,大清的体面还在。”
郑孝胥立在一旁,接过话头时眼神锐利如旧:“宝琛公所言极是。臣已着人清点内库,
当年孝钦显皇后(慈禧)备下的龙凤褂、东珠朝珠虽有损耗,修补后仍可启用。
仪仗、鼓乐须从京郊旗营调派,那些子弟还留着辫子,走在街上,便是活的念想。”
溥仪坐在铺着明黄色软垫的宝座上,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扶手的龙纹雕刻。
他刚过十六周岁,声音里还带着少年人的清朗,却刻意端着沉稳:“可民国政府那边……”
“皇上放心。”陈宝琛欠身道,“优待条件里写得明白,‘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
大婚依旧制,本就是约法所许。
臣已托人递话给步军统领衙门,只说‘内廷喜事,不扰外间’,他们断不敢驳。”
郑孝胥从袖中取出一纸清单,展开时纸张微微作响:
“臣已拟了章程:纳采用的金如意要用沈阳故宫存的旧物,取‘故土不忘’之意。
迎亲仪仗须过长安街,让百姓见见銮驾。
宴席分‘上八珍’‘下八珍’,厨子从前门外‘聚贤楼’请,那掌柜的父亲是光绪爷的御厨,规矩熟。”
溥仪抬眼望向窗外,宫墙内的银杏叶正落得满地金黄,像铺了层碎金。
他轻轻颔,指尖停止了摩挲:“就依二位师傅的意思办。总要让他们知道,这宫墙里,还是有皇上的。”
1922年溥仪的大婚,说是"逊帝"私事,实则是保皇派们憋着劲儿搞的一场政治秀。
这群前清遗老把婚礼当成了宣传的阵地,恨不得把所有能搬出来的封建礼制都堆上去。
就为了向世人证明:“咱们的小皇帝还在,大清的体面就没丢。”
为了凑够婚礼钱,这群人差点把故宫的门槛都当了。
载涛带头把家里的古玩字画拿去变卖,陈宝琛跑到天津租界跟遗老们募捐。
当时溥仪看见账上写着“打造金册银册耗费二十万两”,皱眉说“太浪费”。
陈宝琛立马跪下来磕头:“陛下,这不是浪费,是国体啊!没有这些,何以彰显皇家威仪?”
听说皇上选后,有女孩子人家忙乎开了,都想把女儿送进宫享福。
不过保皇派们对条件抠得很严。他们死活不让溥仪选汉女,说“满汉不通婚乃祖制”,最后敲定正白旗的婉蓉为皇后,
文绣是镶黄旗,当陪嫁妃子,一后一妃,全合老规矩来。
迎亲队伍必须走东华门,就因为这是“皇家专用通道”。
为此载涛专门跑去跟民国政府交涉,软磨硬泡了一个月才获批。
“……”
婚礼当天,保皇派们的表演更是拉满。
前内阁学士耆龄穿着早已过时的朝服,在东华门跪着哭“圣驾”,哭得假牙都掉了。
康有为特意从上海赶来,带着一群弟子在街边焚香跪拜,嘴里念叨“天佑大清”。
连已经改穿西装的辜鸿铭,都硬是找出件马褂穿上,说“要给皇上撑场子”。
他们还特意邀请了不少外国使节,想让“国际社会”看看“大清皇帝”的排场。
英国公使艾斯顿来的时候,载涛亲自跑去门口迎接,指着宫里的仪仗说:
![捡猫后走上人生巅峰[穿越]+番外](/img/32907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