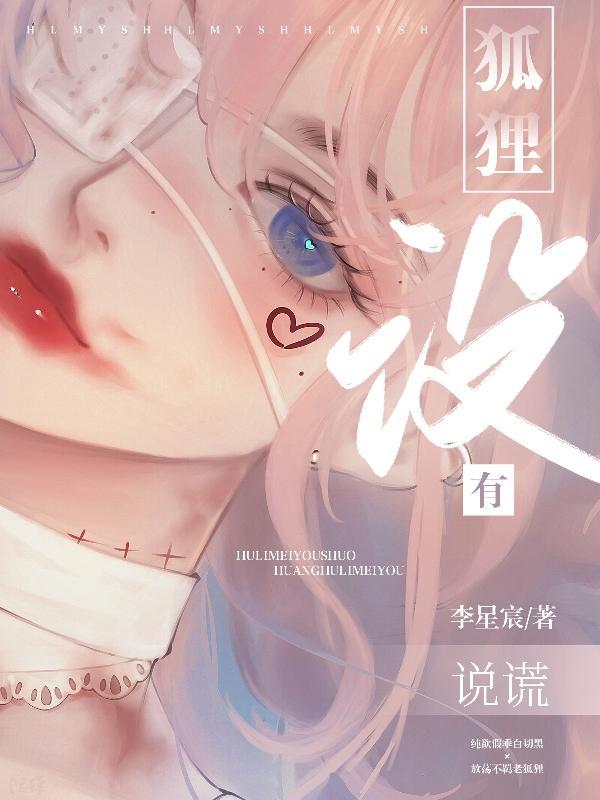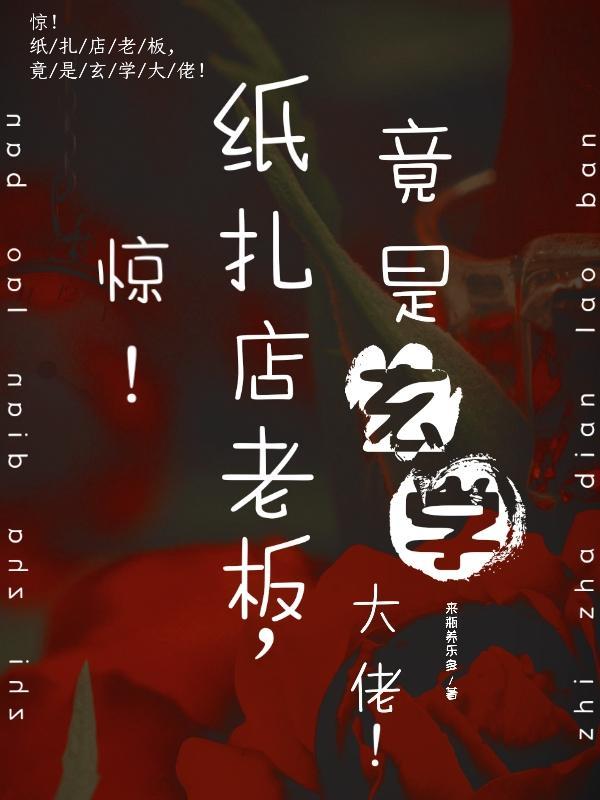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如懿传之凤临天下 > 第5章 和乐(第1页)
第5章 和乐(第1页)
阳光透过慈宁宫雕花的窗棂,细碎地洒在大殿之上,给这庄重的殿堂添了几分柔和。皇帝亲自来到慈宁宫,身后那群侍从脚步整齐又急促,手中捧着的精致匣子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里面装着的正是那本关乎后宫格局的重要册封册子。
当皇帝迈着沉稳的步伐走进慈宁宫的大殿时,太后正端坐在那象征着无上权威的凤椅上。她身着华丽的凤袍,头戴璀璨的凤冠,脸上洋溢着慈祥又和蔼的笑容,那笑容如同春日里的暖阳,让人倍感亲切。皇帝快步上前,双膝跪地,向太后行了一个标准而又恭敬的大礼,动作行云流水,尽显皇家的威严与对太后的敬重。礼毕,他双手小心翼翼地将匣子捧起,恭敬地放在太后的面前,那姿态仿佛捧着的是世间最珍贵的宝物。
太后微笑着,那笑容如同盛开的花朵,带着岁月的从容与智慧。她伸出那保养得极为精致的手,轻轻打开匣子,取出册封册子。册子在她的手中,仿佛是一件需要细细品味的艺术品。她仔细翻阅着,目光在每一个字上停留,那专注的神情仿佛在审视着整个后宫的未来。册子里详细记载了皇帝对几位妃子的册封决定,其中孔氏红葵被册封为贵妃,那贵妃之位在后宫中可是仅次于皇后的尊贵存在;傅恒的侄女富察氏被册封为宁妃,宁字寓意着宁静祥和,想必皇帝对她也有着别样的期许;翰林院掌院学士之女林氏为丽妃,丽字彰显着她的美貌与风采;兆惠将军之女则被册封为恬嫔,恬字给人一种温婉恬静的感觉。
太后缓缓地将册子合上,那动作轻柔而优雅,就像一片羽毛轻轻地飘落,没有出丝毫的声响。然后,太后慢慢地抬起头,她的目光如同深邃的湖水,落在皇帝身上,嘴角泛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那笑容中既有着母亲对儿子的慈爱,就像春日里的微风,轻轻拂过皇帝的心田;又似乎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调侃,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她对皇帝心思的洞察。太后轻声说道:“皇帝啊,你竟然亲自送来册封的册子,这是怕哀家会为难皇后吗?”那声音轻柔却又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皇帝微微一笑,他的笑容中透露出一丝尴尬和无奈,就像被母亲看穿了心思的孩子。他连忙解释道:“母后,您这可真是说笑了。儿臣此举纯粹是想让母后先过目一下,毕竟这册封之事关系重大,儿臣不敢擅自作主。这后宫的安稳关乎着前朝的稳定,儿臣自然是要慎重再慎重。”皇帝说得诚恳,眼神中满是敬畏。
太后听了皇帝的解释,笑着摇了摇头。她的笑声清脆而悦耳,如同银铃般在殿中回荡,却又让人感觉其中蕴含着深意,仿佛藏着无数的智慧与故事。太后说道:“皇帝啊,你可是哀家亲生的,也是我自己亲手养大的。你的性子如何,哀家可是再清楚不过了。这前朝的事务已经够你忙碌的了,你不会在后宫之事上费心的。
你登基这半年来,我自认对得起皇后西林觉罗氏,在你册封她为皇后之后,就将整个后宫大权交给她。她处理的每一件事情,无论对错哀家都一言不,平日里也免了晨昏定省,让她能安心处理后宫诸事。哀家自认我这个婆婆为她做的不错了。”
皇帝微微欠身,神色间带着几分恭谨与诚恳:“母后这般体谅皇后,实乃皇后之福,亦是儿臣之幸。只是此次册封几位妃子,儿臣思来想去,还是觉得应先告知母后,方显对母后的敬重。”
太后轻轻挑眉,目光在皇帝脸上停留片刻,似是在审视他话语中的真假,随后缓缓开口:“皇帝,哀家知晓你心思。只是这后宫之中,平衡之术甚是重要。你此次册封,可曾考虑过各宫之间的和睦?”
皇帝忙点头应道:“母后所言极是,儿臣正是考虑到后宫和睦,才在册封人选上反复斟酌。这孔氏红葵温柔贤淑,富察氏端庄大方,林氏聪慧灵秀,兆惠将军之女恬静温婉,儿臣想着她们各有所长,定能相互扶持,共保后宫安宁。”
太后端坐在那雕琢着繁复凤纹的凤椅之上,周身散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尊贵与威严,宛如一尊不可侵犯的神只。她面无表情地凝视着皇帝永瑚,那双深邃的眼眸犹如幽潭,波澜不惊却又让人难以琢磨其内心真实的想法,仿佛藏着无尽的秘密与算计。
太后端坐在凤椅之上,周身散着不容侵犯的威严,那凤椅上的金丝雕琢的凤凰仿佛也因她的气势而栩栩如生,似要振翅高飞。她缓缓开口,声音虽然平静如水,没有丝毫的波澜,但其中却蕴含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威严,那威严如同无形的压力,缓缓弥漫在整个大殿之中:“啊,你既然也认为哀家对得起皇后西林觉罗氏,将她扶上后位,又给予她诸多体面与尊荣,那么对于你在慈宁宫安插人手一事,哀家倒是可以理解。毕竟你贵为天子,身处这至高无上的位置,为了掌控局势、了解宫中大小事务,有此举动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皇后竟然把手伸进了哀家的慈宁宫,这就让哀家有些费解了。她身为后宫之主,本应谨守本分,协助皇帝管理好后宫,可如今却做出这等越界之事,实在是让哀家心寒呐。”
皇帝心中一惊,犹如平静的湖面突然被投入了一颗巨石,泛起层层涟漪。但他的脸上却不动声色,依旧保持着那副镇定自若的神情,忙道:“母后息怒,儿臣并不知晓皇后有此举动。想必是她一时糊涂,儿臣定会好好教导她,让她明白自己的本分。”
太后冷哼一声,那声音如寒夜中的冷风,刺得人耳膜生疼,“哼,她若真是一时糊涂也就罢了,就怕她是有别的心思。皇帝,你可不要被她蒙蔽了双眼。这后宫之中,人心复杂,你要时刻保持清醒。”
皇帝低头沉思片刻,抬起头时眼神坚定,如夜空中闪烁的寒星,“母后放心,儿臣自会明察秋毫。此次册封之事,也是希望能让后宫多些贤良之人,辅助皇后,共同维护后宫的安稳。至于皇后那边,儿臣会找个机会与她好好谈谈,让她收敛自己的行为。”
太后稍稍停顿了一下,目光在皇帝脸上停留了片刻,那目光犹如两把利刃,似乎在审视着他话语中的真诚,又似乎在整理思绪。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那叹息声中带着一丝无奈与感慨,继续说道,声音中多了几分柔和却又依旧坚定:“永钰这孩子自六岁起便去了西五所,跟随南书房的师傅们读书学习,那西五所虽是清净之地,可对于一个孩子来说,终究是少了些家的温暖。
璟清当年为了江山社稷和亲蒙古,与勇亲王拉旺多尔济回了蒙古,那蒙古之地,风沙漫天,远离故土,她一个弱女子,为了这大清的安稳,背井离乡,其中的艰辛又有谁能知晓。而哀家身边,就只有和乐这么一个女儿相伴左右。和乐也是你的亲妹妹,她天真烂漫,心地善良,从不惹是生非,这就碍了谁的眼?竟有人要如此针对她,甚至把手伸到哀家的慈宁宫来。
皇帝神色一紧,赶忙离座,躬身急道:“母后,儿臣绝无此意!和乐乃是儿臣血脉至亲,儿臣疼爱尚且不及,怎会容旁人碍她眼。这其中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妄图挑拨儿臣与母后、和乐之间的亲情,还望母后明察。”
太后目光冷冷扫过皇帝,那目光仿佛能穿透人的灵魂,冷哼一声:“挑拨?皇帝,哀家倒想问问,若非有人在背后怂恿,皇后怎会有如此胆量,把手伸到哀家的慈宁宫来?哀家虽不管后宫琐事,但也不代表可以任人欺凌到头上。”
皇帝额头上冒出细密汗珠,那汗珠顺着脸颊缓缓滑落,心中暗自懊恼,不知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让太后知晓了此事。他强自镇定,再次深深一揖,那腰弯得如同一张拉满的弓:“母后息怒,儿臣回去定会严查此事。若真是皇后所为,儿臣定不会偏袒,定会给母后一个满意交代。只是如今,还望母后莫要气坏了身子。”
太后微微眯起眼睛,盯着皇帝看了片刻,那眼神犹如深邃的幽潭,让人看不透其中的想法。缓缓说道,声音虽轻却如重锤般敲在皇帝的心上:“皇帝,哀家如今就这一个女儿在身边,若是有人敢对和乐不利,哀家绝不会轻饶。不管是谁,在哀家这里,都没有情面可讲。”
“皇帝,哀家知道你坐在这龙椅上不易,既要平衡前朝后宫,又要顾全大局。但哀家也有自己的底线,和乐便是哀家的底线。和乐平安长大不必和亲蒙古,这是哀家的底线。想当年,璟清历经和亲之苦,远嫁他乡,那其中的孤寂与酸楚,只有自己知晓。如今,哀家绝不愿让和乐再走这条路。皇帝,你可要明白哀家的心意。”
皇帝闻言,神色愈恭谨,连忙再次躬身,声音带着几分恳切:“母后所言,儿臣铭记于心。和乐是儿臣的亲妹妹,儿臣定会拼尽全力护她周全。此次皇后之事,儿臣定会查个水落石出,若真有她涉足其中,儿臣定依宫规处置,绝不姑息。
前朝事务繁杂,儿臣时常顾此失彼,对后宫之事多有疏忽,这才让有心之人钻了空子。儿臣回去后,定会重新梳理后宫事务,整顿宫规,让那些心怀不轨之人无机可乘。
母后为这大清操劳一生,如今本该安享清福,却还要为和乐之事忧心,是儿臣之过。儿臣在此向母后保证,日后定会多花心思在后宫,绝不再让此类事情生,让母后能安心颐养天年。”
太后听完之后,原本紧绷的神色略微放松了一些,但她的眼眸深处仍然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她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地开口说道:“皇帝啊,哀家希望你所说的都是真心话。这后宫若是能够安稳太平,那么前朝自然也会少去许多后顾之忧。和乐虽然身为女子,但她同样也是哀家的心头肉啊!你若是真的能够保护好她,让她平安无事,那哀家自然会感到无比欣慰。”
太后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着接下来要说的话。她凝视着皇帝,继续说道:“你是哀家的亲生儿子,而你的弟弟妹妹们还年幼,他们将来的依靠就只有你一个人了。”
皇帝连忙点头,“儿臣定不辜负母后期望。”
太后的目光缓缓地转向窗外,仿佛透过那扇窗户,她能看到遥远的过去。她的思绪渐渐飘远,回忆起当年璟清远嫁时的情景,心中不禁涌起一阵自责。
“当年璟清远嫁,哀家时常自责。这和乐,说什么也不能再受那份苦了。”太后的声音带着些许惆怅,她的目光落在皇帝身上,继续说道,“皇帝,你也该为妹妹的终身大事好好谋划一番。”
皇帝略微思索了一下,然后回答道:“儿臣会留意合适的人选,定要给和乐寻个如意郎君,让她不必远嫁受苦。”
太后听了皇帝的话,微微颔,表示满意。接着,她又将话题转到了后宫上,“还有这后宫,你既要安抚好皇后,又要让她知道规矩。这新册封的几位妃子,你也要平衡好关系,莫让后宫再生事端。”
皇帝连忙欠身,表示明白太后的意思,“儿臣省得,定会权衡各方,让后宫和睦。”
太后最后看了皇帝一眼,眼神中透露出对他的信任和期望,“你去吧,哀家相信你能处理好这些事。”
皇帝再次行礼,然后带着侍从缓缓退出了慈宁宫。他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自盘算着如何解决这后宫与妹妹之事。这两件事都关系到宫廷的稳定和家族的荣誉,他必须慎重对待,不能有丝毫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