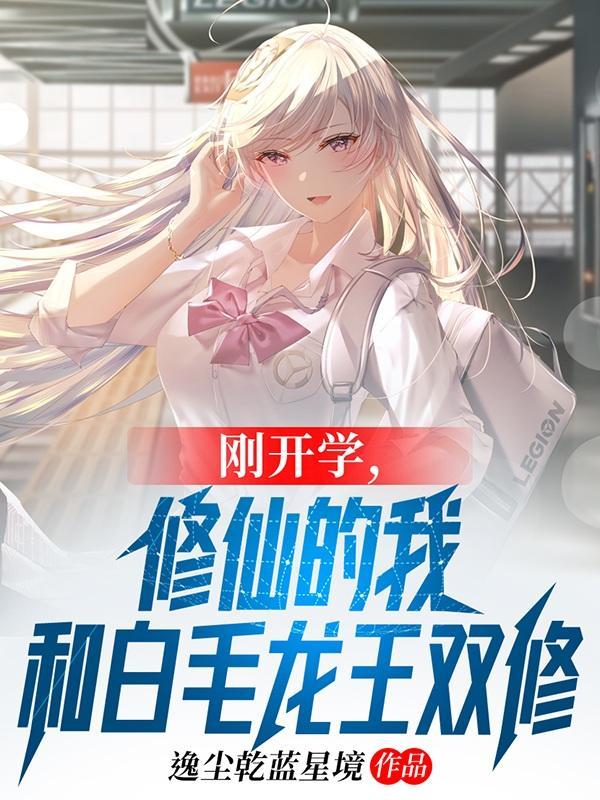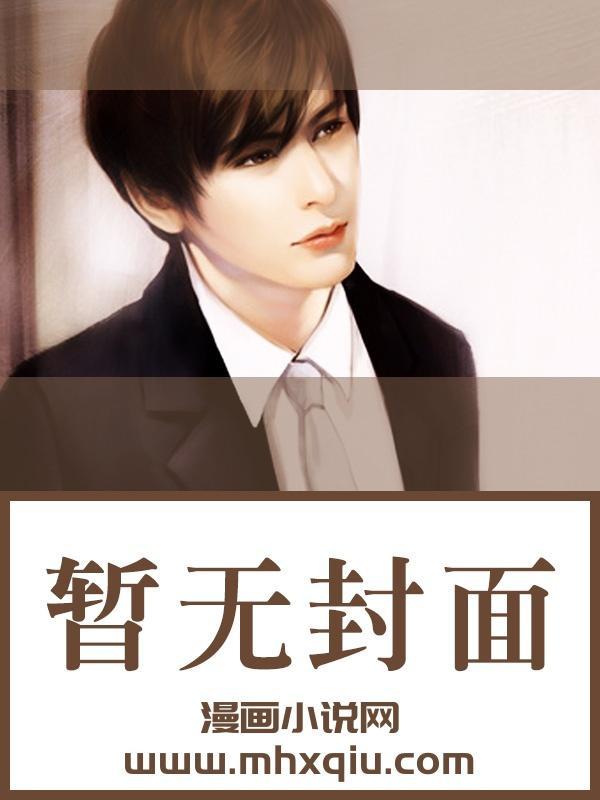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天青之道法自然 > 第12章 病在上焦(第2页)
第12章 病在上焦(第2页)
这话说的,大家都有嘴,都有直接向官家呈笺上报的权利,且不是你自己打小报告就能讨来便宜的。
说这中间没有人协调麽?
有,宰相便是。不过宋没有宰相一职,只有“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宰相之权。但是,又是个二府的制度。“左仆射”只能协调中书省下六部。
调兵赈灾?那是枢密院的事。而且枢密院只管兵。具体统兵权?那的归三衙。
所以,这宰相之位的“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看似个位极人臣,其实的地位也是蛮尴尬的。
有没有能力好的宰相协调此类事情?
倒是有,需有这三司、刑判、枢密、三衙经历之人从中协调。也就是这三个部门都熟悉。比如哲宗朝的章惇章子厚,此人便是独相一个也。
处理天灾这般的突事件,且是需要强大的前瞻性、预知性,和异于常人的组织、策划、执行能力。
而且,能行得仗义,做得小人。亦也知道,这钱从哪来,到哪里去。
各司条例,管辖如何,能做到烂熟于心,且有能知人善任,通晓物资钱粮统筹规划。
什么事找什么人,可用之人在哪?手里有没有人才储备?这人能干什么样的事?需要什么样的支援?
有了这些个条件之后,还要熟读律法,知道如何惩治奸小,宽严并济。
又能识得轻重缓急,熟知各地状况。各路节度使、安抚使、指挥使的人脉关系。才能做到一个协调。因为军队各地都有屯军备粮、军粮储备。一旦灾情形成,各地驻军倒是赈灾方便且最直接有效。
如此,没个几十年官场历练,和军政一体,强大到变态的人脉关系,断不可为之。
且,如此行事倒是容易引起那检察部门的注意,如这御史台定会派员进行监察。
一旦有人弹劾,这“大臣擅权”自那宋太祖之时,便是一个为人臣之大忌!
别说什么“忠臣”因为赵匡胤这货原本就是个后周的“忠臣”,最后被部下“硬”给了一个“黄袍加身”。
都是别人玩剩下的,再玩?就不是很礼貌了。
等你赈完别人的灾了,你的灾难,便也是一个接踵而至。运气极好的,也得一个致仕。于野下,过那诗酒田园。
但凡能在这些规则,和潜规则中生存下来,并且,还能有余力以民为重者,方可称为良相。
且不是没事干处理几个贪官,审理几个冤案让百姓称之为“某某青天”了账。
况且,这官员贪渎,百姓民、刑,均有各司审理案件。小点的有各地刑狱提刑,大点的还有开封府,大理寺。
官员犯罪,有谏院、御史台。宗室作恶,有宗正寺。
“上打昏君,下斩谗臣”这事,也只有戏文里面有。那玩意儿,跟现在的爽文差不多。哄一下脑子坏掉的人还行,暂时麻醉一下也不是不可。看多了,那叫一个毁人心智!
而且北宋斩人犯,地方且是不能擅权。别说北宋,死刑这事,到现在地方也说了不算,必须经过最高法。
需刑部下派提刑官到各地勘察无误后勾签,也叫勾决。
而且,不是罪案罪大恶极者,不能就地问斩当时就给砍了。得等到秋后,给罪犯一个上诉的机会。
遇到“临刑喊冤者不可斩”,还要还地方重审。
而这王公犯法自有宗正寺查办,官员贪腐且得有谏院收集证据,然后,交由御史台查办。
那龙、虎、狗三口铡刀历史上有没有姑且不说。
但凡从有法律开始,无论任何王朝那都是绝对的杜绝专权私刑。
因为死刑也是有规定的,按律为之。
恰恰是无论任何时候的律法先是杜绝私刑的,因为私刑专权为法之大患也。
即便是执法者再不要脸面,也得有所顾忌。且不敢如此明目张胆明火执仗的弄出个私刑杀人。
话不多说,书归正传。
此时那吕维倒是一个头两个大。
那熟读的《罗织经》《度心术》在此倒是不太管用。
那玩意儿在和平时期耍个心计斗个心眼,算计个谁,争权夺利还能有些个用处。
但,在这灾、疫、战、乱之时且是一点用都全无啊!
你去罗织敌人的罪行?不用你罗织便是一大堆。人家刀都砍到脖子了,你且去度他心下如何去想?
开玩笑。倒是不用去猜,砍了你取了级邀功!他看你的级便是金钱,便是美女,便是封妻荫子。和你能从那圣贤之书中看到颜如玉、黄金屋一个道理,仅此而已。
天灾?别说是你,现在的科学家绑在一起,都不能参透这天地到底是个什么脾气。
那这诸如《罗织经》《度心术》此类之书便是糟粕?
也不算吧?
先,我不承认文化有什么糟粕,只不过是人们对它的用处有了误解。
读圣贤书,听孔孟之言倒是能让人道貌岸然,但丝毫不会妨碍他心下的那些男盗女娼。
如此便是圣人之言教化不灵,大贤之书误人子弟乎?
这话会说的,哲学的两面性不能强加到文化上吧?
这是两码事。
过去听过一个老“教授”的讲座,其间,此翁有言“儒家所倡之‘仁义礼智信’全是糟粕,是奴役人民的学说。应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