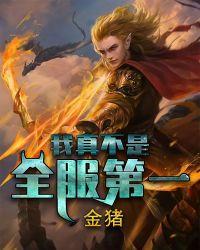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 > 第918章 高祖武皇帝四(第1页)
第918章 高祖武皇帝四(第1页)
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戊戌年)
春天正月甲子日,北魏封氐族领杨定为阴平王。
北魏秦州的羌人反叛。
二月癸巳日,安成康王萧秀去世。萧秀虽然和梁武帝是平民时的兄弟,但成为君臣之后,他小心谨慎、敬畏的态度,比那些关系疏远、地位低下的臣子还要厉害,梁武帝因此越觉得他贤能。萧秀和弟弟始兴王萧憺特别友爱,萧憺长期担任荆州刺史,常常把自己的俸禄分一半给萧秀,萧秀坦然接受,也不觉得多了不好意思。
甲辰日,梁朝大赦天下。
己酉日,北魏大赦天下,改年号为神龟。
北魏东益州的氐人反叛。
北魏皇帝接见柔然的使者,责备他们藩国礼仪不周到,商议要依照汉朝对待匈奴的旧例,派使者回访。司农少卿张伦上表,认为:“太祖开创帝业,每天都忙不过来,所以才让柔然这小子在一方游荡。这也是因为中原地区多有忧患,重视华夏事务而对夷狄之事有所放松。高祖当时致力于向南展,没时间北伐。世宗遵循先帝遗志,对于柔然使者的到来,只接受他们的朝见而不回复。当时认为圣明的皇帝统治天下,国家富强、兵力强盛,对于与敌国交往的礼仪,有什么可害怕而不敢做的,又有什么需求而一定要去做呢!现在柔然虽然仰慕我们的德行而来,但也是想看看我们的强弱;如果让朝廷使者奉命到柔然王庭,与他们称兄道弟,恐怕不符合祖宗的本意。如果事情实在不得已,应该下诏书,向他们展示上下的礼仪规范,命令宰臣写信,向他们说明归顺的道理,观察他们的态度,再慢慢用恩威来决定如何对待他们,这样王者的体统就端正了。怎么能因为柔然等戎狄的势力有所变化,就马上损害国家的礼仪制度呢!”皇帝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张伦是张白泽的儿子。
三月辛未日,北魏灵寿武敬公于忠去世。
北魏南秦州的氐人反叛。朝廷派龙骧将军崔袭持符节去劝谕他们。
夏天四月丁酉日,北魏秦文宣公胡国珍去世,朝廷追赠他假黄钺、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封号为太上秦公,加赐九锡,用特殊的礼仪安葬他,赠送丧服和仪仗护卫,待遇极其优厚。又把太后母亲皇甫氏的灵柩迎来,与胡国珍合葬,称皇甫氏为太上秦孝穆君。谏议大夫常山人张普惠认为,前代皇后的父亲没有称“太上”的,“太上”这个名号不能用于臣子,他到宫门前上疏陈述自己的看法,皇帝身边的人都不敢为他通报。正好胡家在挖墓穴时,下面有块大石头,张普惠于是秘密上表,认为:“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主,‘太上’这个称呼是因为有‘上’才产生的,皇太后称‘令’是延续皇帝的‘敕’以向下传达旨意,大概是遵循妇人三从的道理,就像周武王时的文母,能位列辅佐武王的十位贤能之人当中,现在司徒(胡国珍)称‘太上’,恐怕违背了延续皇帝敕令的本意。孔子说:‘一定要名正言顺啊!’最近选墓地定吉兆,却因为这块石头而改变占卜结果,这或许是天地神灵在以此出重要警示,启圣上的情思。希望能停止使用这个冒犯君上的名号,以祈求上天的福佑。”太后于是亲自到胡国珍的宅邸,召集五品以上官员广泛讨论。王公大臣们都迎合太后的心意,争相诘问刁难张普惠;但张普惠随机应变,进行辨析,没人能让他屈服。太后派元叉向张普惠传达旨意说:“我这么做,是出于孝子的心意。你所陈述的,是忠臣的道理。各位大臣已经有了决议,你不能强行改变我的想法。以后你有什么见解,不要有顾虑,尽管说出来。”
太后为太上君建造寺庙,其壮丽程度与永宁寺相当。
尚书上奏要恢复征收百姓的绵麻税,张普惠上疏,认为:“高祖废除大斗,不用长尺,更改沉重的秤,是为了爱护百姓、减轻赋税。考虑到国家军队需要绵麻,所以在绢税上增加绵八两,在布税上增加麻十五斤,百姓因为称和尺减小,觉得减少的不止绵麻的价值,所以都乐意缴纳赋税。从那以后,所征收的绢布,逐渐又变得又长又宽,百姓哀怨之声,朝野都能听到。宰辅大臣不追究根源在于布幅加宽、长度增加,就急忙停止征收绵麻税。不久后尚书又因为国家用度不足,想再次征收。这是丢弃天下的大信,废弃自己已经施行的诏令,重蹈以前的错误,会被后世的史书批评。他们不想想库中有大量的麻,其实是群臣私自侵占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百姓缴纳的物品,有的一斤多出百铢,没听说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去治州郡的罪;可要是稍微有点质量不好,就治户主的罪,还连累三长。所以库中的绢布,过规定尺寸的很多,大臣们领取俸禄,人人都追求绢布又长又宽、厚实,不再有标准限制,也没听说有人因为绢布幅面有多余的尺寸,就要求还给官府的。现在想要恢复征收绵麻税,应当先统一称和尺,明确立下严格的禁令,不许再放任尺寸增加,让天下人知道皇上和太后爱护百姓、珍惜法律到这种程度,那么太和年间的好政策就能在神龟年间再次出现了。”
张普惠又因为北魏皇帝喜欢在苑囿游玩打猎,不亲自上朝处理政务,过于尊崇佛法,把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事大多委托给有关部门,上疏恳切劝谏,认为:“致力于那些不可捉摸的佛教修行,耗费大量钱财在百姓身上,减少官员俸禄、征用民力,来供奉这些无所事事的僧人,大肆装饰寺庙宫殿,希望获得渺茫的回报,黎明时大臣们在宫外恭敬行礼,而众多僧人却在宫内悠闲游玩,这样的礼仪违背了时代的要求,人神都不能和睦。我认为与其追求早晚诵经礼佛的因果,祈求难以预料的善果,不如赢得天下人的欢心来侍奉亲人,使天下太平,灾害不生。希望陛下能注重自身的言行举止,为各国做出表率,亲自虔诚地参加祭祀天地和祖先的仪式,亲自履行初一、十五的礼仪,在太学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典礼,尽心尽力重视农业生产。酌情减少那些不急用的寺庙装饰,恢复百官长期被削减的俸禄。已经建造的务必简约并尽快完工,还没建造的就一律不再建造。这样的话,孝顺友爱就能通达神明,道德教化就能光照四海,节约用度、爱护百姓,法律和风俗都能从中受益。”不久后,皇帝下令让大臣们讨论祭祀先圣先师的礼仪,而且从这以后每月接见群臣一次,这些都是采纳了张普惠的建议。
张普惠又上表论述时政的得失,太后和皇帝把张普惠召到宣光殿,针对他表中的内容进行诘问。
临川王萧宏妾室的弟弟吴法寿杀了人,藏在萧宏的府中,梁武帝下令萧宏交出他,吴法寿当天就伏法认罪。御史台奏请免除萧宏的官职,梁武帝批示说:“爱护萧宏是出于兄弟间的私情,免除萧宏官职是为了维护王者的正法。所奏请的可以批准。”五月戊寅日,司徒、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临川王萧宏被免职。
【内核解读】
这段天监十七年(公元518年)的史事,如同一面多棱镜,折射出南北朝时期政治、民族、社会的复杂面相,其中诸多细节值得从现代视角审视:
权力场域中的礼法博弈
北魏胡国珍葬礼引的称号之争,本质是皇权与礼制传统的角力。张普惠以天无二日为由反对人臣称,背后是儒家思想对皇权垄断性的维护。而胡太后以孝子之志回应,既凸显了外戚势力借扩张权力的策略,也暴露了礼制在现实政治中的弹性——当权力需要时,传统可被解释、也可被突破。这种礼法为权力服务的逻辑,在后世王朝中反复上演。
南梁临川王宏因庇护杀人的妾弟被免官,梁武帝兄弟私亲王者正法的区分,看似彰显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公平,实则暗藏帝王权术:既维护了法律权威,又以之说保留了对宗室的宽容,这种选择性执法恰是专制皇权的典型特征——法律的刚性永远让位于权力的弹性。
民族关系中的身份焦虑
北魏对柔然使者的态度争议,折射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碰撞中的身份困境。张伦反对与为昆弟的主张,本质是华夏中心论夷夏之辨的坚守,认为与游牧政权平等交往是亏典礼。这种观念背后,既有对自身文化优越性的自信,也暗含对游牧民族军事威胁的恐惧。而北魏最终的选择,又显示出实用主义的考量——当国力不足以碾压对手时,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成为无奈之举。
氐、羌等族群的接连反叛,则揭示了北魏民族治理的深层矛盾。征服王朝在统治多民族地区时,若仅靠军事镇压而缺乏文化融合与利益共享,必然陷入反叛—镇压—再反叛的恶性循环。这也为后世提供了镜鉴:民族问题的核心从来不是,而是。
社会治理中的制度悖论
北魏张普惠关于绵麻税的奏疏,揭露了税收制度的变形记:孝文帝改革本以爱民薄赋为初衷,通过调整度量衡减轻百姓负担,但基层执行中却通过幅广度长暗中加征,最终导致百姓嗟怨。这种政策善意执行恶意的背离,印证了一个现代治理命题:制度设计若缺乏刚性监督,再好的初衷也会被基层权力异化。
他呼吁先正称尺,明立严禁,实则指向了标准化治理的重要性——税收、度量衡的统一透明,是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平的基础。这一思想与现代税收法定、计量标准化理念不谋而合,可见治理的智慧具有跨越时代的共通性。
信仰与现实的资源争夺
胡太后为母造寺壮丽埒于永宁,与张普惠减禄削力供无事之僧的批评,形成了信仰狂热与民生现实的尖锐对立。当国家将大量资源投入宗教建设,甚至挤压官员俸禄与民生开支时,宗教便从精神寄托异化为权力炫示的工具。张普惠收万国之欢心以事其亲的谏言,本质是呼吁将有限资源从虚无的来世实在的民生,这种重现实轻虚玄的务实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启示意义。
而北魏孝明帝好游骋苑囿,不亲视朝的怠政,与过崇佛法形成呼应——当最高统治者沉迷享乐与虚玄信仰,政权的运转必然出现失灵。这也印证了一个历史规律:权力失去约束、统治者脱离现实,往往是王朝衰落的开端。
结语:历史中的现代性因子
这段史料看似是遥远的古代叙事,却蕴含着诸多与现代社会相通的治理命题:如何平衡权力与制度、如何处理多民族关系、如何实现政策善意与执行效果的统一、如何分配信仰与民生的资源。从这些历史细节中,我们能看到人性的恒常与制度的演进——正是这些跨越时空的治理困境破局尝试,构成了历史留给现代的宝贵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