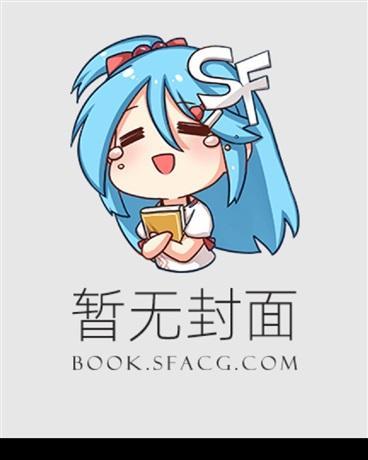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 > 第168章 求仁得仁 夫子的抉择(第1页)
第168章 求仁得仁 夫子的抉择(第1页)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鲁哀公二年深秋的卫国都城帝丘,驿馆庭院里的梧桐叶被北风卷成旋儿,冉有搓着冻红的手问子贡:“夫子为卫君乎?”他的狐裘袖口已磨出毛边,说话时呼出的白气与暮色交融。子贡望着孔子房间透出的烛火在窗纸上摇曳,那光晕里还映着竹简翻动的影子,低声说:“诺,吾将问之。”
子贡推门而入时,孔子正对着《周易》的“讼卦”沉思,竹简上的“天与水违行”墨迹未干,案头还摆着刚研好的墨锭。他躬身行礼,问:“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放下手中的蓍草,指尖在卦象上停顿:“古之贤人也。”“怨乎?”子贡追问,目光落在夫子鬓角新添的白上——自离开鲁国后,这白便以肉眼可见的度生长。孔子忽然笑了,那笑意从眼角的皱纹里漫出来:“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子贡退出驿馆时,北风卷着落叶打在廊柱上,出簌簌声响。他对冉有说:“夫子不为也。”冉有望着远处戚邑的方向——蒯聩的军队正在那里集结,篝火像散落的星子,忽然明白:夫子的“不为”不是骑墙,而是以伯夷、叔齐的“让”,给这场“争”立了面镜子。《论语?述而》记载的这段对话,藏着儒家“以仁为归”的伦理密码:子贡以古人古事迂回设问,孔子以“求仁得仁”直抵核心,二者的默契印证了“仁”是判断是非的终极标准。从卫国驿馆的烛火到当代社会的伦理考场,这种“求仁得仁”的智慧始终是心灵的指南针。
一、卫国乱局:君位之争的伦理困局
卫君辄与父亲蒯聩的权力争夺,像一把锈蚀的斧钺劈开了春秋晚期的宗法制度。卫灵公三十九年,太子蒯聩因不满南子与宋朝私通,派家臣戏阳刺杀南子,事败后“出奔宋,又之晋,托于赵简子”(《左传?定公十四年》),这一逃便是十三年。灵公晚年欲立少子郢为储,郢却叩推辞:“郢异于他子。且君没于吾手,若有之,郢必闻之。且亡人之子辄在。”(《左传?哀公二年》)——他既不愿违背宗法,又念及流亡在外的侄子辄,最终卫人立辄为君,即卫出公。
鲁哀公二年,蒯聩在赵简子的支持下,率晋军盘踞戚邑(今河南濮阳北),派使者向儿子要回君位。辄派大夫石曼姑率军驻守边境,父子俩隔着黄河对峙,形成“父居戚,子居帝丘,遥遥相望如敌国”(《史记?卫康叔世家》)的僵局。卫国大夫公孙丁叹息:“父不父,子不子,何以国为?”(《公羊传?哀公三年》)这场乱局中,每个人都被卷进伦理漩涡:石曼姑辅佐辄是“忠”却违“孝”,百姓夹在父子间是“顺”却失“义”,连孔子的弟子们也陷入困惑。
孔子周游列国期间两至卫国,对局势的肌理洞若观火。第一次在鲁定公十三年,卫灵公问他“军旅之事”,孔子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次日便离开——他看穿灵公想借他的声望巩固军事野心。第二次在鲁哀公二年,此时辄已继位五年,蒯聩在戚邑囤积粮草,双方剑拔弩张。《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卫灵公夫人南子派人对孔子说:“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再三,不得已而见之,“入门,北面稽。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这场会面让子路很不高兴,孔子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他既需维持与卫国的关系,又不愿与失德者同流合污,处境如履薄冰。
“夫子为卫君乎”的“为”,在《尔雅?释诂》中释为“助也”,冉有的疑问直指孔子是否辅佐卫君辄。春秋时期“士无定主”,但辅佐需符合“义”,正如《论语?先进》“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卫君辄拒父归国违背“孝道”,蒯聩以子拒父违背“臣道”,二者皆有可议之处。冉有曾随孔子参与齐鲁夹谷之会,见过夫子如何以礼挫败齐国阴谋,此刻却看不清这场父子相残的乱局中,“道”该如何安放。
卫国的乱局是春秋“礼崩乐坏”的典型切片。《礼记?檀弓》记载“蒯聩之入卫也,载其而归”——后来蒯聩攻入帝丘时,竟将辄的党羽公孙弥牟的级载于车中示众,亲情早已被权力吞噬。孔子曾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卫国的“萧墙之祸”印证了他的预见:当宗法制度失去“仁”的内核,礼便成了空壳,最终必然崩塌。
二、子贡问仁:迂回中的智慧锋芒
子贡选择以“伯夷、叔齐”设问,像一位老练的工匠,用最温润的玉石打磨最锋利的刀刃。他深知直接问“夫子是否支持卫君”会陷入两难:若夫子肯定,则违背“孝”;若否定,则可能得罪卫君。这种迂回战术,与《礼记?经解》“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的方法一脉相承——通过类比彰显是非,让答案自现。
子贡的智慧并非偶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他“利口巧辞”,曾代表鲁国出使齐国,“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靠的正是这种“以迂为直”的辩才。此刻他选择伯夷、叔齐,因这二人的故事在春秋时期是公认的“道德标杆”,《诗经?小雅?采薇》便暗咏其“不食周粟”之事,连山野村夫都能道出梗概。
伯夷、叔齐是孤竹君的两个儿子,父临终前指定叔齐继位。《史记?伯夷列传》记载:“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二人逃离时带走的只有一箪一瓢,在阳山采薇为生。周武王伐纣时,他们“扣马而谏”:“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史记?伯夷列传》)武王灭商后,他们“义不食周粟,隐于阳山,采薇而食之”,最终饿死在山中。他们的“让”与卫君的“争”形成伦理两极:一个为道义放弃权位,一个为权位背弃亲情。
“怨乎?”子贡的提问像探骊得珠,直击行为的动机与结果。他想知道:伯夷、叔齐付出饿死的代价,是否后悔?若有怨,则其行为的价值存疑;若无怨,则证明“仁”的价值越生死。孔子的回答“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将行为的意义锚定在“求仁”的过程——他们追求的是“让国”的仁,最终实现了这一价值,故无怨无悔。
子贡退出驿馆时,北风更紧了,他对冉有说:“夫子不为也。”这个判断包含三层推理:伯夷、叔齐因“让”被称为贤人,卫君因“争”违背仁;夫子肯定前者,故必否定后者;“不为”不是弃权,而是坚守仁的底线。这种“闻一知二”的洞察力,让冉有想起子贡曾说“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论语?子张》),此刻他才窥见这“墙内”的一角风光。
三、求仁得仁:孔子的伦理标尺
“求仁而得仁”的“求”是主动追寻,“得”是价值实现,二者构成完整的伦理闭环。在孔子看来,道德价值不取决于结果是否“有利”,而取决于动机是否“合仁”。伯夷、叔齐的“求”是“让国”,符合“孝悌”之仁;他们的“得”不是君位,而是“仁”的实现,故“又何怨”。这种“动机论”的伦理观,与《论语?颜渊》“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主张一致——仁的实现全在自身选择,与外在评价无关。
“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最高道德准则,像一棵大树,“孝悌”是根,“爱人”是干,“礼敬”是叶。针对卫国局势,“仁”具体表现为“父慈子孝”“君礼臣忠”。卫君辄拒父归国,违背“孝”;蒯聩以武力争位,违背“礼”;双方都脱离了“仁”的根基,故孔子“不为也”。
对比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更可见“求仁得仁”的灵活性。管仲辅佐公子纠失败后,转而辅佐齐桓公,按“忠臣不事二主”的标准是“不仁”。但孔子却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左衽矣。”(《论语?宪问》)因管仲的“求”是“安民”,符合“爱人”之仁,故虽有瑕疵仍被肯定。这说明孔子的“仁”不是僵化教条,而是看核心动机是否合于“爱人利众”。
“求仁得仁”对后世的伦理选择影响深远。孟子将其展为“舍生取义”:“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文天祥兵败被俘后,在狱中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追求的“仁”是民族气节,最终“得仁”于柴市;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被贬伊犁,写下“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的“求”是国家利益,“得”的是民心所向。这些人都在用生命诠释:“得仁”不在于结局是否圆满,而在于是否坚守初心。
四、孔子的政治伦理:以仁为归的抉择
孔子的政治伦理以“正名”为根基,《论语?子路》记载他对冉有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卫国的问题先是“名不正”:辄作为儿子拒父归国,违背“子道”;蒯聩作为臣子以武力争位,违背“臣道”。孔子认为,若不先纠正名分,任何治理都是徒劳。
他在卫国的言行始终坚守“仁”的底线。第一次至卫时,“卫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史记?孔子世家》)。南子的车驾用翠羽装饰,雍渠的宦官服饰僭越礼制,孔子望着街市上百姓的指指点点,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他可以忍受贫困,却不能忍受道义被践踏。
第二次至卫时,“卫君欲得孔子为政”,孔子提出的条件是“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他要求先明确辄与蒯聩的名分:若立辄,则需以“祖父遗命”为由,妥善安置蒯聩;若迎回蒯聩,则辄需退居臣位。这一主张看似迂腐,实则是治乱的根本——没有名分的正义,任何权力都是流沙上的楼阁。
孔子的“不为也”包含着积极的抗争。他不辅佐卫君,却通过评价伯夷、叔齐传递立场,让弟子们明白“争”的危害;他在卫国收徒讲学,将“仁礼”之道播撒民间;晚年整理《春秋》时,对“卫世子蒯聩出奔”“卫出公辄拒父”等事件“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暗含褒贬。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的精神,让“不为也”不是消极逃避,而是以自身的“仁”对抗现实的“不义”。
五、历史回响:求仁得仁的多元实践
季札让国的“延陵高风”,与伯夷、叔齐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吴王寿梦有四子:诸樊、余祭、余眜、季札。季札最贤,寿梦欲立他,“季札让不可,乃立长子诸樊”(《史记?吴太伯世家》)。诸樊临终前遗命“兄终弟及”,想最终传位给季札。余祭、余眜依次继位,轮到季札时,他“弃其室而耕”,逃到延陵(今江苏常州)种田,宁愿做农夫也不违心继位。孔子南巡时见季札墓,题字“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赞其“让国”如伯夷。季札的“求仁”是“不贪权位”,“得仁”是“全身全名”,证明“求仁得仁”并非一定要付出生命代价。
屈原的“上下而求索”,展现了求仁不得仍坚守的悲壮。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辅佐楚怀王时主张“联齐抗秦”,却遭上官大夫谗言,被流放汉北。《离骚》中“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呐喊,道出他的“求仁”是楚国的“美政”。秦将白起攻破郢都时,他“被行吟泽畔”,渔夫劝他“随其流而扬其波”,他却“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屈原虽未“得仁”于生前,却在死后成为“爱国”的象征,其精神价值越了政治成败——这种“求仁”的过程本身,已是“得仁”的另一种形态。
苏轼的“进退自如”,体现了求仁得仁的通达。他任杭州知州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浚治,宋兴,废之,葑积为田”(《宋史?苏轼传》),导致旱季无水、雨季成涝。他率百姓“浚西湖,筑长堤,自南至北,横亘湖中”,这条“苏堤”至今滋养杭州。被贬黄州时,他“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在“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困境中,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苏轼的“求仁”是“利民”与“自安”,无论顺逆都坚守本心,这种“得仁”不在外物,而在内心的安宁。
六、伦理困境的现代映射:求仁得仁的当代诠释
政治领域的“权力伦理”仍在演绎着“争”与“让”的抉择。2o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团队被曝“通俄门”,试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选票;而奥巴马在卸任时说:“权力是借来的,必须还给人民。”前者的“争”违背“服务公众”的初心,后者的“让”符合“仁”的本质。孔子的“不为也”提醒从政者:权力的价值在于“求仁”(公共利益),而非满足私欲,否则再高的职位都是道德的负数。
职场中的“职业伦理”面临着类似的考验。某三甲医院的外科主任,收红包、拿回扣,虽技术精湛却被患者称为“手术刀上的蛀虫”;而乡村医生支月英“几十年坚守在偏远山村讲台,从‘支姐姐’到‘支妈妈’”(感动中国颁奖词),月薪不足三千却照亮大山里的童年。前者的“争”(私利)让职业蒙羞,后者的“求仁”(育人)让平凡伟大,正如伯夷、叔齐的“让”虽无权力,却赢得千古尊重。
家庭中的“孝悌伦理”常陷入“卫君式”的困局。某卫视调解节目中,兄弟三人因父亲房产分配大打出手,甚至伪造遗嘱;而武汉的一对环卫工夫妇,“每天凌晨4点起床工作,供三个孩子上大学,说‘只要孩子们好,再累都值’”。前者的“争”撕裂亲情,后者的“求仁”(付出)滋养家庭,证明“仁”的本质不是利益分配,而是“爱人”的初心。
科技伦理中的“创新与责任”需要“求仁得仁”的平衡。某互联网公司为抢占市场,推出“大数据杀熟”算法,利用用户信息牟利;而“北斗团队”二十年如一日,“攻克16o余项核心技术,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自主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简史》)。前者的“争”(利润)违背科技伦理,后者的“求仁”(强国)实现价值,正如孔子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科技的价值最终由“仁”来评判。
七、子贡的智慧:伦理推理的艺术
子贡的“闻一知二”展现了儒家“类推”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在《论语》中多次体现。子夏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答“绘事后素”,子夏立刻领悟“礼后乎”(《论语?八佾》),从绘画类推到礼乐;子贡从伯夷、叔齐的“让”类推到卫君的“争”,正是这种思维的运用。在信息不充分或不便直言的情况下,类推是传递立场的有效方式,正如《周易?系辞》“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子贡的沟通智慧对现代人际交往仍有启示。在商务谈判中,直接指责对方“违约”易引对抗,而说“我们合作多年,一直遵循‘互利’原则”则更易达成共识;家庭中妻子想提醒丈夫少抽烟,不说“你不要命了”,而说“爸当年就是抽烟伤了肺,我怕你……”,效果往往更好。这种“迂回策略”的核心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像子贡那样抓住“仁”的本质,让对方自悟,正如《论语?先进》“夫子循循然善诱人”,最高明的沟通是引导对方现答案。
子贡的“知言”能力源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深刻把握。他曾问孔子:“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瑚琏是宗庙重器,子贡明白这是说他“有大用”但需“在礼的框架内”。这种理解让他能从“求仁得仁”的只言片语中,准确把握孔子对卫君的态度。现代社会的有效沟通也需如此——不仅听对方说什么,更要理解其背后的价值观,正如子贡与孔子的默契,基于对“仁”的共同坚守。
八、求仁得仁的本质:动机与结果的辩证
“求仁得仁”的本质是“动机优先”的伦理观,与康德的“善良意志”异曲同工。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说:“在世界之中,甚至在世界之外,除了善良意志,不可能设想一个无条件善的东西。”孔子评价伯夷、叔齐,正是看其“让国”的善良意志,而非“饿死”的结果;评价管仲,也是看其“安民”的动机,而非“事二主”的行为。这种伦理观提醒我们:评价一个人,应看“他为什么做”,而非“他做成了什么”。
“得仁”的多元形态证明仁的实践不拘一格。文天祥的“仁”是民族气节,范仲淹的“仁”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王顺友的“仁”是“二十年行走在雪域高原,成为马班邮路上的忠诚信使”(感动中国颁奖词)。正如《周易?系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只要方向是“仁”,不同的道路都能抵达“得仁”的终点。
动机与结果的辩证统一是更高的境界。孔子既重动机(求仁),也不忽视结果(利民),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现代社会的公益组织“免费午餐”,既怀着“让贫困儿童吃饱饭”的初心(求仁),又建立了透明的财务制度确保每分钱都用在孩子身上(得仁),这种“动机与结果并重”是“求仁得仁”的现代展。
九、求仁得仁的终极意义:在抉择中成就自我
“求仁得仁”的终极意义是通过伦理抉择实现自我的道德完善。伯夷、叔齐通过“让国”成为“贤人”,孔子通过“传道”成为“圣人”,普通人也可通过日常的“仁行”成就自我。北京的“快递小哥”汪勇,在疫情期间“从一个人接送医护人员,到组织起志愿者车队”(感动中国颁奖词),他的“求仁”(助人)让平凡闪耀;杭州的“拾荒老人”韦思浩,“匿名捐款十余年,资助了多名贫困学生”,他的“求仁”(奉献)让卑微崇高。
在价值多元的现代社会,“求仁得仁”为我们提供了锚点。面对“躺平”与“内卷”的困境,选择“真诚工作、认真生活”便是“求仁”,内心的安宁便是“得仁”;面对“利己”与“利他”的纠结,“举手之劳帮助他人”便是“求仁”,人际关系的温暖便是“得仁”。这种抉择不需要惊天动地,却能在平凡中雕刻出人性的光辉。
孔子的“不为也”与伯夷、叔齐的“让国”,共同指向“自由”的本质——不是随心所欲,而是能选择符合“仁”的行为,即使面临压力也不妥协。这种“道德自由”比外在的自由更根本,正如《庄子?逍遥游》“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最高的自由是越外在评价,坚守内心的“仁”。
从卫国驿馆的烛火到当代社会的灯火,“求仁得仁”的智慧始终照耀着伦理抉择的道路。它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站在哪个位置,而是如何到达那里;不是获得了什么,而是成为了什么样的人。当我们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犹豫时,不妨回想子贡的提问与孔子的回答——求仁得仁,又何怨?这或许就是穿越千年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