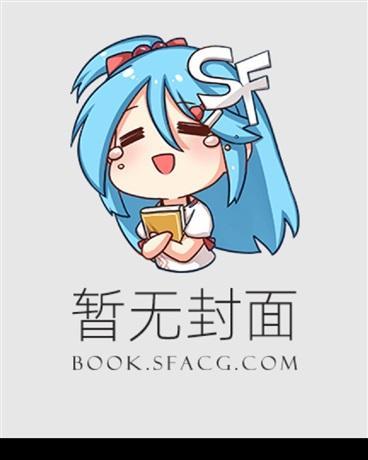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 > 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 夫子的取舍(第1页)
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 夫子的取舍(第1页)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鲁定公十三年的暮春,孔子在卫国的蒲邑市集上驻足。执鞭官吏正挥动漆成红色的荆条,驱赶着满载盐车的黄牛穿过人群,车轴转动出“吱呀”的声响,扬起的尘土落在孔子的麻布袍上,留下细密的灰痕。子贡用袖子掸去夫子肩头的尘土,指着那官吏说:“夫子,彼执鞭者,月得五秉粟,不足为贵。”孔子却望着官吏腰间悬挂的铜刀——那是市集守门人查验货物的工具,缓缓摇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记载的这句箴言,像一枚打磨光滑的青铜钱:正面铸着“求富”的坦然,背面刻着“从好”的坚守。“富而可求”不是拜金的贪婪,而是对正当财富的认可——即使是被贵族轻视的执鞭之职,只要能通过合法劳动获利,亦不排斥;“如不可求”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对不义之财的决绝拒绝,转而坚守内心的精神追求。这种对财富的清醒认知,藏着儒家“义利之辨”的密码:财富是滋养生活的甘泉,而非淹没人性的洪水,正如《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区别不在是否求利,而在是否以义为舟。从孔子的市集驻足到当代的职场抉择,这种“求富与从心”的平衡始终是人生航向的罗盘。
一、富而可求:财富的正当性边界
“富而可求”的“可求”,核心在“可”字——指符合道义、能够追求的正当途径。《说文解字》“可,肯也”,意为“值得、允许”,在儒家语境中,“可求”的财富需通过“义”的三重检验:手段合法(非欺诈掠夺)、符合礼制(不僭越等级)、利于他人(不独善其身)。孔子不否认财富的价值,《礼记?礼运》“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财富是满足“饮食”等基本欲望的基础,“可求”正是对这种合理性的承认,正如《周易?系辞》“变通者,趋时也”,顺应正当途径求富,是对时势的尊重。
春秋时期的“富”与“求”,有明确的伦理约束与计量标准。《周礼?天官?大宰》将“利”分为“九利”,“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皆为按土地等级征收的正当收入,其中“什一税”(收获的十分之一)是通行标准。据《管子?轻重甲》记载,当时成年男子“月食四石”(约今8o斤),“执鞭之士”月得“五秉粟”(一秉为十六斛,五秉即八十斛,约今16oo斤),除去上缴官府的部分,实际所得可养活五口之家,这种“劳而获”的财富被孔子认可。而“聚敛者”如季氏“富于周公”(《论语?先进》),通过“田赋倍增”(《左传?哀公十一年》)掠夺财富,则被批评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执鞭之士”的职业象征,暗含对职业平等的深刻认可。“执鞭”在春秋时期有两种具体形态:一是市场守门人“执鞭以击商贾”(《周礼?地官?司市》),负责查验货物、征收市税,《诗经?小雅?瞻彼洛矣》“鞸琫有珌,驷铁孔阜”描述的就是这类官吏的装束;二是马车护卫“执鞭以驱马”(《礼记?曲礼》),为贵族出行驾车,《论语?乡党》“升车,必正立,执绥”中的“绥”便是他们递给主人的登车绳。这两种职业皆属“庶人在官者”,地位低于士阶层,《礼记?王制》“庶人在官者,禄足以代其耕也”,明确其收入仅够替代耕作所得。孔子说“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打破了“君子不亲小事”的贵族偏见,承认任何职业只要正当,都值得尊重,这种职业平等观比《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的分类更具突破性,直指“职业无高低,唯在合义”。
“可求”的财富有明确的禁区与警示。《论语?子路》记载孔子反对“欲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小利”即通过短视手段获取的不义之财,如《左传?昭公十六年》郑国子产揭露的“韩起买玉环”事件,商人与大夫勾结偷税,便是典型的“小利”。《左传?襄公二十八年》更明确“不义而富,谓之盗”,将不义之富等同于盗窃。孔子在卫国时,卫灵公夫人南子“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史记?孔子世家》),见南子可能带来政治利益(如获得卫国重用),但因南子“通于宋朝”(《左传?定公十四年》)的秽行,孔子虽礼节性见之却“子路不说”,事后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可见“不可求”的底线不可突破——财富诱惑再大,也不能违背基本伦理。
二、如不可求:坚守的底气与智慧
“如不可求”的“不可求”,特指不符合道义的财富,即《论语?里仁》“放于利而行,多怨”的“利”——通过欺诈(如商人“以次充好”)、掠夺(如官吏“横征暴敛”)、谄媚(如近臣“邀宠固位”)等手段获得的财富。孔子认为,对这类财富应坚决拒绝,正如《孟子?滕文公下》“富贵不能淫”,不义之富会腐蚀人格,比贫困更可怕。《论语?阳货》记载的阳货馈豚事件极具代表性:阳货是鲁国权臣,“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其财富来源不正,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既不失礼又不结交,巧妙避开不义之财的诱惑。
“从吾所好”的“好”,是越物质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实现。《说文解字》“好,美也”,在孔子语境中特指“道”的践行——“士志于道”(《论语?里仁》),“所好”包括“学而不厌”的求知(《论语?述而》)、“诲人不倦”的教学(《论语?述而》)、“克己复礼”的修身(《论语?颜渊》)。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正是“从吾所好”的典范,其“乐”源于对“道”的追求,而非物质满足。这种“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论语?先进》记载“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师生二人因“所好”相同而产生深度共鸣。
“不可求”时的坚守,需强大的内心支撑与精神储备。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论语?卫灵公》),子路愠怒质疑:“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却“讲诵弦歌不衰”,这种“穷而不滥”的底气来自三重支撑:对“道”的信念(“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对历史的认知(“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对自身的期许(“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礼记?儒行》记载儒者“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正是这种坚守的写照,孔子在“斥乎齐,逐乎宋卫”的困境中,始终保持“君子固穷”的尊严,证明精神力量能越物质匮乏。
“从吾所好”不是消极避世,而是积极的价值创造与传承。孔子“退而修《诗》《书》,定《礼》《乐》”(《史记?孔子世家》),将“所好”转化为文化工程:整理《诗经》删去重复篇目,保留“思无邪”的3o5篇;修订《礼记》规范“冠婚丧祭”之礼,使其“可达于王道”;编纂《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史载道。这种“所好”虽无财富回报,却产生了比财富更持久的影响——正如《论语?学而》“德不孤,必有邻”,子夏“在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子贡“存鲁乱齐”,弟子们将“所好”扬光大,形成越物质的价值共同体。
三、义利之辨:儒家财富观的核心架构
“富而可求”与“如不可求”的背后,是“义利之辨”的永恒命题与动态平衡。孔子的态度既非墨家“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的功利主义——墨家“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将利作为核心驱动力;也非道家“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第十九章》)的虚无主义——道家认为利是社会混乱的根源;而是“见利思义”(《论语?宪问》)的中庸之道——承认利的合理性,更强调义的优先性,正如《周易?乾卦》“利者,义之和也”,正当利益是道义调和的自然结果。
“义”对“利”的约束与引导,体现在具体情境的细致考量中。《论语?子罕》记载子贡“货殖焉,亿则屡中”,孔子不反对其经商,因子贡的“利”符合三重义:一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获利同时“存鲁乱齐”,以商业手段实现政治目的;二是“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资助孔子周游列国,帮助贫困弟子;三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论语?学而》)——虽“家累千金”却保持谦逊。而对冉有“为季氏聚敛”,孔子则怒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因冉有的“利”违背三重义:过度征税违背“敛从其薄”(《左传?哀公十一年》)的古制;助纣为虐违背“季氏旅于泰山”的僭越批判;损害民生违背“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的主张。可见儒家反对的不是利本身,而是“见利忘义”的失衡。
“义利之辨”的现代转化与跨文明呼应,展现其普遍价值。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市场机制的同时,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这种对“道德约束市场”的认知与孔子“见利思义”相通。当代企业家“取之有道,用之有节”的实践更显其生命力:曹德旺创办福耀玻璃“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可求),同时“累计捐款16o亿元”用于教育与扶贫(从义),提出“企业家若没有责任感,充其量是富豪”;比尔?盖茨“通过微软创新获利”(可求),又“捐出全部财产致力于全球健康”(从义),证明财富与责任可并行不悖,这种实践正是对“义利之辨”的现代诠释。
四、孔子的财富实践:言行一致的生活哲学
孔子对“可求之富”的接纳与享用,体现在生活细节的自然流露中,既不刻意苦行也不奢靡浪费。《论语?乡党》记载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稻米舂得不够精就不食,鱼肉切得不够细就不食,这种对饮食品质的追求需一定财富支撑;“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祭祀用的肉过三天就不食用,注重健康与礼仪的平衡。他任鲁国大司寇时“奉粟六万”(《史记?孔子世家》)——据清代学者崔述考证,六万粟约合今
斤,相当于当时大夫的标准俸禄,孔子坦然接受,因这是“行道”的物质基础,正如《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推行德政需要稳定的物质保障。
孔子对“不可求之富”的拒绝与警惕,彰显原则底线与人格独立。《论语?阳货》记载阳货“馈孔子豚”——阳货是把持鲁国政权的乱臣,其馈赠带有政治拉拢意图,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趁阳货外出时回访,既不失礼又保持距离;《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齐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给予封地意味着依附齐国,因晏婴反对“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而作罢,孔子“遂行,反乎鲁”,不贪恋封地之富。这种“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坚守,使其在贫富贵贱中保持人格完整,正如《论语?子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被财富绑架意志。
孔子“从吾所好”的实践,越物质局限,展现精神富足的强大力量。周游列国时“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却仍“讲诵弦歌不衰”(《史记?孔子世家》),用礼乐精神凝聚弟子;在卫国匡地被围困“拘焉五日”,仍向弟子阐释“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以文化自信化解危机。晚年返鲁后“删《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史记?孔子世家》),将“所好”转化为系统的文化工程:《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史记?太史公自序》),以史明义;《周易》“韦编三绝”,探索宇宙人生之道。这种“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的状态,证明精神追求能带来越财富的满足感,正如《周易?系辞》“乐天知命,故不忧”。
四、历史回响:义利之辨的传承谱系与时代演绎
孟子对“义利”的展,提出“先义后利”的系统主张,强化义的优先性。《孟子?梁惠王上》“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看似否定利,实则反对“上下交征利”的恶性循环——“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认为先利后义会导致道德崩坏。他认可“可求之富”的合理性:“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主张通过农业生产实现财富增长;同时强调“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将孔子的义利观系统化、绝对化,形成“舍生取义”(《孟子?告子上》)的价值排序。
荀子以“礼义”规范财富分配,构建“义利两有”的现实路径。《荀子?荣辱》“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明确义利先后的荣辱标准;《荀子?富国》“足国之道,节用而裕民,而善臧其余”,主张通过“强本而节用”(展农业、节约开支)实现国家与民众的财富增长。他在《正名》中区分“正利”与“邪利”:“正义而为谓之行,匿行而利谓之污”,符合礼义的行为即使获利也是正当,隐匿行为追求利益则是污浊。荀子本人“三为祭酒”(《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在稷下学宫享受“列大夫”待遇,坦然接受正当俸禄,同时“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将财富用于学术研究,实践了“义利两有”的主张。
汉代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将义利对立推向极致,强化义的神圣性。《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他对策时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主张追求道义而非利益,阐明大道而非功利,这种思想服务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需求——通过强化义的优先性,维护大一统秩序。董仲舒任江都相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史记?儒林列传》),拒绝以方术邀宠获利,实践了“从吾所好”;他“居家着书,有客来谒,辄称病不见”(《汉书?董仲舒传》),不通过社交获取财富,保持学术独立,其义利观虽有矫枉过正,却巩固了“义为利本”的儒家传统。
宋代朱熹的“义利之辨”,融合理学思想,构建“天理”框架下的财富观。他在《论语集注》中注解“富而可求”时说:“富若可求,则虽贱役亦为之;若不可求,则亦无所愧悔,而乐吾所好也。”强调“可求”的核心在“理”——符合天理的富可求,违背天理的富不可求,“天理”即“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法则。朱熹本人“布衣蔬食,与诸生讲学”(《宋史?朱熹传》),任焕章阁待制时“俸给皆以养亲及周族党”(《朱文公文集》),将俸禄用于赡养亲人、周济族人;创办白鹿洞书院时“请赐九经,复访得书院故址,奏复之”(《宋史?朱熹传》),将“所好”的教育事业置于财富之上,其“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在财富观上表现为“寡欲”而非“无欲”——合理的物质需求是天理,过度的财富追求是人欲。
明代王阳明以“心学”诠释义利,回归“良知”本体的直觉判断。他认为“心即理”,“义利之分,只在一念之间”(《传习录》),“可求之富”是“良知”认可的利——“如好好色,如恶恶臭”的自然判断;“不可求”是良知排斥的利——违背本心的贪婪。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正德皇帝“赐玺书金币”,他“固辞,乞归省”(《明史?王守仁传》),拒绝过度封赏;在赣州推行“十家牌法”时“身率以俭,与士民共甘苦”(《王阳明年谱》),不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他在龙场驿“凿石椁以居”,却“悟格物致知之旨”,证明“从吾所好”能在极端贫困中实现精神富足,其义利观强调“知行合一”——知道义利之分,更要在行动中践行。
五、历史人物的财富抉择:义利平衡的生动实践
范蠡的“三聚三散”,完美演绎“富而可求,从吾所好”的财富智慧与人生境界。他助勾践灭吴后“乘扁舟浮于江湖”(《史记?货殖列传》),拒绝越国“分国而王之”的封赏,因“大名之下,难以久居”(《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深知功高震主的危险,选择“可求”的商业致富;在齐国“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积累“数十万”资产,被齐王任为相,却“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史记?货殖列传》)——第一次散财,回归布衣;至陶地“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改名陶朱公“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史记?货殖列传》)——第二、三次散财,最终“至陶,为朱公,寿终,故世传曰陶朱公”。范蠡的“求富”不贪——“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史记?货殖列传》),只取合理利润;“从好”不迂——将财富用于“救济贫弱”,实现“富行其德”(《史记?货殖列传》),是孔子财富观的完美实践。
白居易的“中隐”生活,在仕宦与隐逸间找到平衡,拓展“从吾所好”的内涵与形式。任江州司马时“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江州司马厅记》),坦然接受俸禄——这是“可求”的正当收入;同时“吏隐”于官,在《中隐》诗中提出“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不追求高位厚禄,选择清闲官职,以便“退衙之后,焚香操琴,读书赋诗”。他在《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悲悯,在《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同情,将“所好”的诗歌创作与民生关怀结合。白居易晚年“罢刑部侍郎,以刑部尚书致仕”(《旧唐书?白居易传》),“卖马市宅,俭以自奉”,将积蓄用于“治佛光寺,凿龙门八节滩”(《新唐书?白居易传》),既不贪恋财富,也不消极避世,这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状态,展现了“求富与从心”的世俗智慧。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将财富追求升华为社会责任,赋予“可求”与“从好”更广阔的格局。他“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宋史?范仲淹传》),任参知政事时推行“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试图通过改革实现“行道”的理想;获俸禄后“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范文正公义田记》),规定“族中子弟有嫁娶者,给钱二十千;丧葬者,给钱三十千”,将“可求之富”转化为“所好”的公益实践。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胸怀使财富成为践行道义的工具:他“在杭兴水利,疏西湖,溉田千顷”(《宋史?范仲淹传》),用俸禄资助公共工程;“帅邠州,作大顺城,以拒西夏”(《宋史?范仲淹传》),将财富用于国防建设。他晚年“居邓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范仲淹答“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宋史?范仲淹传》),证明精神追求能越物质欲望,其财富观已越个人得失,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儒家理想。
张謇的“实业救国”,在近代转型中融合求富与从心,赋予传统义利观新的时代内涵。清末他“以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却在甲午战败后“弃官从商”,因“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张謇全集》)——将“可求”的财富追求与“从好”的救国理想结合。1895年创办大生纱厂,章程规定“厂中盈余,除提存保险公积金外,分十三股:以六股为股东红利,三股为办事者花红,四股为地方公益”(《大生纱厂章程》),明确财富分配兼顾股东、员工与社会;他提出“父教育,母实业”的主张,用纱厂利润创办通州师范学校、南通博物苑,“所办实业、教育、慈善等事,经费皆取诸大生”(《张謇传》)。张謇说“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张謇日记》),这种“所好”已越个人,与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相通,证明传统义利观能适应近代社会变革。
六、“执鞭之士”的现代诠释:职业尊严与价值重构
“执鞭之士”在当代的多元象征,是“正当职业皆可敬”的平等理念。无论是快递员、环卫工人还是流水线工人,只要通过劳动获利,都值得尊重。“快递小哥”汪勇在2o2o年疫情期间,从“一个人接送医护”到“组织3o人志愿者车队”,再到“建立餐食供应链,每天供餐1。5万份”(《武汉快递小哥汪勇:守护抗疫医护的凡人英雄》),既通过服务获得合理收入(可求),又践行社会责任(从好),被评为“感动中国2o2o年度人物”。环卫工人李萌“放弃白领工作,选择环卫事业”,负责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的清扫,“每天步行3万步,清运垃圾16桶”(《全国劳动模范李萌:用扫帚书写青春》),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她的话“工作没有高低贵贱,把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正是对“执鞭之士”精神的现代诠释。
职业平等的制度保障与社会认同,持续打破“执鞭”的贵贱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为职业平等提供法律基础;2o19年国务院印《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提升“执鞭”类职业的社会地位。北大毕业生陈生“放弃公务员岗位,卖猪肉创立壹号土猪品牌”,建立“屠夫学校”培养专业人才,年销售额1o亿元(《北大屠夫陈生:把猪肉卖出北大水平》);名校博士黄文秀“放弃大城市工作,返乡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种植砂糖橘,修建蓄水池,脱贫195户883人”(《黄文秀:青春之花绽放在扶贫路上》),他们选择的“执鞭”式职业,因“可求”且“从好”而获得社会认可,正如孔子所言“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
“执鞭”的精神内核与现代转化,是“敬业乐群”的职业态度与“工匠精神”的追求。日本“寿司之神”小野二郎“一生悬命做寿司”,9o岁仍坚持在银座的小店工作,“对食材的挑选近乎苛刻——章鱼要按摩5o分钟,米饭温度要与人体一致”(《寿司之神》纪录片),将简单职业做到极致(可求);同时“对客人的尊重无微不至——记得每位客人的座位偏好、是否左撇子”(《寿司之神》),这种“工匠精神”与孔子“执事敬”(《论语?子路》)的态度一致——职业无贵贱,敬业即崇高。中国“火箭焊接大师”高凤林“为火箭动机焊接,38年焊出13o多枚火箭”,“焊缝宽度误差不过o。1毫米,相当于头丝的15”(《大国工匠高凤林:焊接火箭的“金手”》),他的“执鞭”是焊接技术,却因敬业与创新,为国家航天事业做出贡献,证明“执鞭”职业能创造非凡价值。
七、当代致富与坚守:义利平衡的多元实践
企业家的“合法经营,回馈社会”,在商业成功中践行“可求”与“从好”的平衡。曹德旺创办福耀玻璃“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打破国外垄断,“全球市场份额达31%”(《曹德旺:心若菩提》),既获商业成功(可求);同时“累计捐款16o亿元,用于教育、扶贫、救灾”,2o21年“成立河仁慈善基金会,捐出福耀玻璃1o%股份”(《曹德旺慈善之路》),践行社会责任(从好),他提出“企业家若没有责任感,充其量是富豪”,明确财富与责任的关系。任正非“华为不上市,聚焦技术研”,“2o22年研投入1615亿元,占营收22。4%”(《华为年报》),既获商业成功(可求),又坚守“科技自立”(从好),“华为鸿蒙系统打破安卓垄断”,实现“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织”的愿景,这些实践证明财富与责任可并行不悖。
普通人的“勤劳务实,坚守初心”,在平凡岗位上体现义利平衡的真实温度。外卖骑手雷海为“送餐之余读诗,随身携带《唐诗宋词选》,等餐时读,休息时背”,2o18年获《中国诗词大会》第三季冠军(《外卖骑手雷海为:在诗词中寻找力量》),他的“求富”是勤劳送餐(可求),“从好”是诗词热爱(从心),这种平衡让平凡生活充满诗意。教师张桂梅“创办华坪女高,免费招收贫困女孩”,“工资、奖金、捐款全部用于办学,身患23种疾病仍坚持上课”(《张桂梅:大山里的“燃灯者”》),她的“可求”是合理工资,“从好”是“让女孩走出大山”的教育理想,证明平凡岗位上的义利平衡更显真实动人。
科技工作者的“技术致富,为国争光”,拓展“可求”边界,实现更高层次的“从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一生扎根稻田,9o岁仍在海南育种”(《袁隆平传》),既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共和国勋章”等荣誉与奖励(可求),又实现“让中国人吃饱饭”“禾下乘凉梦”(从好)的理想。“芯片专家”胡伟武“带领团队研龙芯芯片,打破国外垄断”,“2o22年龙芯处理器出货量15oo万颗,用于政务、能源等领域”(《龙芯:自主创新的芯片之路》),他拒绝国外高薪诱惑,“从吾所好”的科技自立,使个人价值与国家利益相结合,这种“所好”关乎国家命脉,越个人财富。
八、义利之辨的现代价值:对抗拜金与虚无的精神武器
“富而可求”对抗“拜金主义”的极端与异化。拜金主义将财富视为唯一价值标准,如“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的扭曲观念,将物质凌驾于情感之上;而“可求”强调“取之有道”“用之有节”,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提醒财富是手段而非目的。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生理需求”(财富满足)作为基础,更高层次是“自我实现”,与孔子“富而可求”后追求“从吾所好”相通——财富是实现自我的工具,而非终极目标。当代“极简主义”生活方式的流行,“断舍离”非必要消费,专注“真正需要”,也是对拜金主义的反思,与“可求”的适度原则一致。
“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对抗“虚无主义”的消极与颓废。虚无主义认为“一切皆无意义”,放弃对价值的追求,如“躺平”文化中的极端者——“不工作、不消费、不社交”,否定奋斗的意义;而“从吾所好”主张在财富之外寻找意义,如“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理想主义,“采菊东篱下”的审美追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关怀,这些“所好”能支撑人在贫困中保持尊严,正如《论语?卫灵公》“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贫困中坚守操守,小人则会放纵堕落。当代“志愿服务”的兴起,“9o后”“oo后”参与支教、环保、救灾等公益活动,在“无利可图”中获得价值感,正是“从吾所好”的现代实践。
“义利平衡”的现代意义,在于构建健康的个体财富观与社会价值体系。社会层面需完善“合法致富”的制度环境(保障可求)——加强产权保护,打击非法获利;倡导“社会责任”的文化氛围(鼓励从好)——通过税收优惠、荣誉表彰激励公益行为。个人层面需明确“什么值得追求”——财富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真正的幸福在于“求富”的正当性与“从好”的充实感,正如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提出的“心流”理论,最幸福的时刻是全情投入“所好”的活动,而非获得财富的瞬间。孔子在市集上的驻足,既不鄙夷执鞭者的卑微,也不羡慕不义者的富贵,只在义利之间守住本心,这种智慧对当代人仍有深刻启示。
九、求富与从心的终极意义:人生的自主与自由
“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的终极意义,是承认物质基础的合理性,打破“重义轻利”的道德虚伪——儒家从不主张“安贫乐道”的刻意苦行,而是“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的自然状态,贫困时不怨天尤人,富贵时不失谦逊礼仪。“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则是肯定精神追求的越性,拒绝“唯利是图”的价值低俗——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正在于有越物质的精神需求,正如《礼记?曲礼》“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
从孔子的市集抉择到当代的人生选择,“求富与从心”的智慧始终未变。它告诉我们:财富如舟,道义如舵,无舟难行远,无舵易迷航;“执鞭之士”的价值不在职业高低,而在是否“可求”——是否通过正当途径获利;“从吾所好”的意义不在贫穷富贵,而在是否“甘心”——是否坚守内心的精神追求。正如范仲淹所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种越物质的精神自由,才是“求富与从心”的终极指向。
在这个财富诱惑日益增多的时代,孔子的话语如清泉洗心:“富而可求”是对生活的诚实——承认物质需求的合理性;“从吾所好”是对灵魂的忠诚——坚守精神追求的崇高性。当我们在求职时兼顾收入与兴趣,在致富后不忘责任与初心,在贫困中保持尊严与追求,便是在实践这种古老的智慧——让财富成为支撑理想的基石,而非压垮精神的重负,正如孔子当年望着执鞭者的背影,眼中没有鄙夷,只有对“各得其所”的坦然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