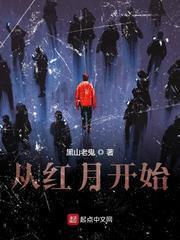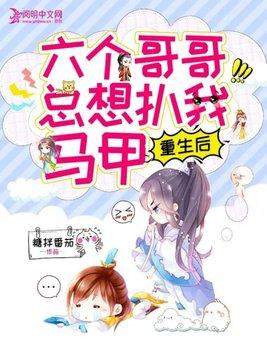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历史的回响:那些震撼人心的话语 > 第134章 陋巷之乐 颜回精神的千年回响(第1页)
第134章 陋巷之乐 颜回精神的千年回响(第1页)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鲁哀公十三年的深秋,曲阜城东南的陋巷飘起了细雨。巷子尽头的茅草屋里,颜回正坐在窗前翻阅竹简,案几上放着一箪糙米、一瓢冷水。寒风从破损的窗棂钻进来,吹动他单薄的衣衫,他却浑然不觉,嘴角还带着一丝浅笑。巷口的邻居看着这一幕,摇头叹息:“这样的日子,换作是我,早就愁白了头。”而此刻,在不远处的杏坛,孔子正对着弟子们赞叹:“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这声跨越两千五百年的赞叹,让陋巷的茅草屋成为中国文化中最动人的精神地标。颜回的“乐”,不是对贫困的麻木,也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一种在物质匮乏中依然充盈的精神状态,一种越外在境遇的内在坚守。从春秋的陋巷到现代的都市,这种“不改其乐”的精神,如同不灭的火种,在每个时代都能点燃人们对精神价值的向往。
一、陋巷考:地理空间与精神家园
要理解颜回的“乐”,先要走进他居住的“陋巷”。这条看似普通的巷子,既是地理空间,也是精神家园,承载着儒家对“安贫乐道”的最初诠释。
陋巷的地理位置:据《曲阜县志》记载,颜回居住的陋巷位于曲阜城东南,今曲阜颜庙东侧,又称“颜子巷”。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泗水》载:“孔庙东南五百步,有颜回宅,宅中有井,井北有台,即颜回当年鼓琴处。”唐代《元和郡县志》更明确记载:“颜回故宅在曲阜县东南三里,陋巷是也。”如今的陋巷虽历经变迁,但仍保留着古朴的风貌,青石板路凹凸不平,两侧的低矮房屋依稀可见当年的简陋。
“陋”的多重含义:“陋”在《说文解字》中释为“厄陕也”,即狭窄、简陋。颜回的陋巷,“陋”不仅指物理空间的狭小破败,更暗含着与外界的隔阂——它远离繁华的市集,也避开了政治的喧嚣,成为一个专注于精神追求的“世外桃源”。这种“陋”是主动选择的结果,正如《庄子?刻意》所言“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颜回在陋巷中找到了精神的自由。
陋巷与孔府的对比:曲阜城中,孔府的富丽堂皇与陋巷的破败简陋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恰如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两种人生境遇。孔府代表着儒家理想的实现,陋巷则象征着儒家精神的坚守。有趣的是,两者相距不过数里,却共同构成了儒家精神的完整图景——既能在庙堂之高践行大道,也能在陋巷之卑守护初心。
在河南卫辉的颜子庙中,有一幅“陋巷图”壁画:画面中央是颜回的茅草屋,周围是狭窄的巷子,远处是曲阜城的轮廓,天空中有祥云缭绕。这幅画将陋巷置于广阔的背景中,暗示着:真正的精神家园,不在于空间的大小,而在于内心的丰盈。
二、一箪一瓢:物质极简与精神丰盈
“一箪食,一瓢饮”是颜回生活的真实写照,这种极致的物质极简,与他丰盈的精神世界形成强烈反差,也为后世树立了“重精神轻物质”的价值标杆。
箪与瓢的文化象征:箪是古代盛饭的竹器,《礼记?曲礼》记载“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可见箪是最普通的食器;瓢是剖开葫芦做成的饮水器,《诗经?小雅?瓠叶》有“幡幡瓠叶,采之亨之”,瓠(葫芦)是平民最常用的器物。颜回选择箪食瓢饮,并非被迫,而是主动摒弃物质的奢华,正如《论语?述而》中孔子所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饮食与德行的关联:儒家将饮食与德行紧密相连,《论语?乡党》详细记载了孔子的饮食规范,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强调饮食的节制与礼仪。颜回的箪食瓢饮,是对这种饮食伦理的极致践行——不是追求食物的精美,而是保持内心的清明。《孔子家语?颜回》记载,颜回曾说“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他的志向不在口腹之欲,而在天下大同。
极简生活的现代呼应:颜回的极简生活,与现代的“极简主义”不谋而合。现代极简主义主张“少即是多”,摒弃不必要的物质欲望,专注于生命的本质。美国作家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自建小屋,过着“一屋、一床、一桌、一椅”的简朴生活,写下《瓦尔登湖》,他在书中说“我们的生命被琐碎消耗殆尽”,这与颜回在陋巷中的选择有着跨越时空的共鸣。
考古现的战国时期“彩绘竹箪”(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制作精美,说明当时的箪并非都粗糙简陋,颜回的“一箪食”很可能是刻意选择的朴素。这种选择告诉我们:物质的简朴不是贫穷的无奈,而是精神自由的前提。
三、人不堪其忧:世俗之忧与圣贤之乐的分野
“人不堪其忧”的“人”,指的是世俗之人,他们的“忧”与颜回的“乐”形成鲜明分野,这种分野揭示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外在的物质追求与内在的精神满足。
世俗之忧的三重表现:
生存之忧:普通人面对箪食瓢饮、陋巷居住的境遇,先担忧的是基本生存,如“明日之食何在”“寒冬如何御寒”。《诗经?豳风?七月》中“无衣无褐,何以卒岁”,正是这种生存之忧的真实写照。
攀比之忧:人在社会中难免相互比较,看到他人锦衣玉食、高屋阔院,再反观自身的简陋,便会产生自卑与焦虑。《韩非子?喻老》中“咎莫大于欲得”,指出欲望是痛苦的根源。
未来之忧:世俗之人常为未来谋划,担忧年老无依、疾病无医,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恐惧,让他们无法安于当下。《论语?卫灵公》中“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反映了这种普遍心态。
颜回之乐的越性:颜回的“乐”并非没有意识到贫困的处境,而是不被这种处境所困扰。他的“乐”有三重境界:
乐道之乐:颜回在孔子的教导中领悟了“道”的真谛,这种精神上的收获让他越物质匮乏,正如《论语?子罕》中孔子所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颜回的“乐”是“仁者不忧”的体现。
自得之乐:他在学习与思考中获得内在的满足,《论语?先进》记载颜回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这种对知识与道德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快乐。
安命之乐:颜回接受自己的物质境遇,不抱怨、不攀比,如《中庸》所言“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在接纳中获得内心的平静。
在山东曲阜的颜庙“乐亭”内,有一副楹联:“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中自甘淡泊;数尺地几间屋于圣人侧共仰光华。”这副楹联准确道出了颜回之乐的本质——不与世俗攀比,只与圣贤对话。
四、回也不改其乐:“乐”的内涵解构
颜回的“乐”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历代学者对其内涵多有阐释,从不同角度揭示这种精神状态的丰富性。
乐道之乐:东汉郑玄注《论语》时说“乐在道,不在贫”,明确指出颜回的乐源于对“道”的追求。这里的“道”即儒家的仁道、礼乐之道,颜回在践行道的过程中获得精神满足。《孔子家语?颜回》记载,颜回曾对孔子说“回闻熏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共国而治,以其类异也。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他的快乐在于对道的信仰与践行。
好学之乐: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并认为这种乐“盖其心有足焉,不以贫窭为忧,而以学道为乐也”。颜回是孔子弟子中最“好学”的一个,《论语?雍也》记载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2过,不幸短命死矣”,对知识的渴求与领悟,让他在陋巷中也能自得其乐。
心斋之乐:庄子虽非儒家,却对颜回的境界多有推崇,《庄子?人间世》记载颜回向孔子请教“心斋”,孔子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颜回的“不改其乐”,与这种“心斋”的虚静状态相通,越了感官的局限,达到内心的澄明。
近代学者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说“颜回的乐,是一种绝对的乐,是于环境的乐”,这种乐不是情绪的波动,而是一种稳定的精神状态,如《周易?系辞》所言“乐天知命,故不忧”。
五、孔子的双重赞叹:“贤哉回也”的深意
孔子对颜回的赞叹重复了两次,这种重复在《论语》中极为罕见,蕴含着孔子对颜回的特殊情感与深刻期许,也反映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推崇。
第一次赞叹:对颜回人格的肯定:“贤哉回也!”的第一个“贤”,指的是颜回在贫困中的坚守。孔子一生周游列国,见过太多为富贵而放弃原则的人,如《论语?里仁》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而颜回在极端贫困中仍能坚守道,这种“贫贱不能移”的品格,让孔子由衷赞叹。
第二次赞叹:对儒家理想的寄托:第二个“贤哉回也!”的赞叹,越了对个人的肯定,指向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孔子看来,颜回的境界是“士志于道”的完美体现,是每个儒生都应追求的目标。《论语?子张》中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而颜回的“学”不为仕,只为道,这种纯粹性让孔子看到了儒家精神传承的希望。
重复赞叹的修辞力量:在文学中,重复是增强情感表达的重要手法。《诗经?周南?关雎》中“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的重复,层层递进表达爱慕之情;孔子对颜回的重复赞叹,则是情感的极致喷,如同《楚辞?离骚》中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将对理想的执着推向顶点。
在山西太原的崇善寺,保存着一幅明代“孔子赞颜回”图轴,画面中孔子手指颜回,面带赞叹之色,颜回则躬身行礼,神情谦逊。这幅画生动再现了“贤哉回也”的场景,也让我们感受到:老师对学生的最高评价,莫过于对其人格与理想的双重认可。
六、颜回的生死:陋巷之乐的短暂与永恒
颜回二十九岁而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他的早逝让陋巷之乐成为短暂的绝响,却也让这种精神获得了永恒的生命力。孔子“哭之恸”,不仅是为弟子的逝去,更是为这种理想人格的早夭而痛惜。
颜回之死的记载:《论语?先进》记载“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孔子的悲痛溢于言表。《孔子家语?颜回》详细记载了颜回的死因:“回年二十九,尽白,蚤死。”结合他“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后世多认为他死于营养不良或过度操劳,这种贫困导致的死亡,让“陋巷之乐”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