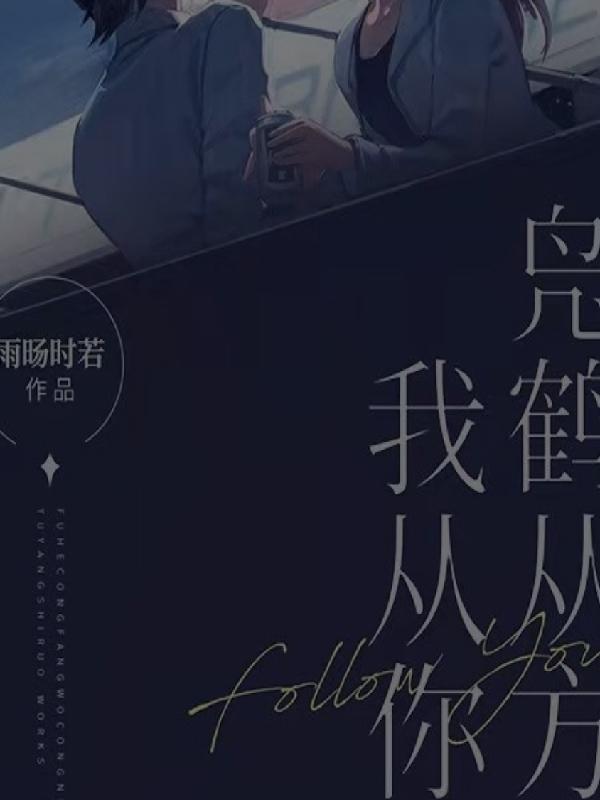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曹操刘备,那些美人是我的 > 第362章 刘备附谏(第1页)
第362章 刘备附谏(第1页)
第二日,晨雾刚散,东平陵外便响起了震天的鼓角。管统登上东门敌楼,远远望见曹操大军列阵于城下,旌旗如林,甲胄映着晨光泛出冷光,前锋步兵持刀盾摆出攻城姿态,却只列阵不动,并无半分冲锋的迹象。
他眉头微蹙,又转身策马赶往西门,袁绍今日兵马只有五千,骑兵环伺、步兵肃立,阵型严整如铁壁,同样只是对峙,连冲车、云梯都未曾向前挪动半步。
管统目光扫过袁军阵列,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佩剑。
两门敌军明明集结了兵力,却只摆开架势不攻城,既不试探虚实,也不叫阵辱骂,安静得反常。
他抬眼望向远方,虽看不到袁军大营,可两门敌军的诡异举动,像一张无形的网,让他心头沉甸甸的。
袁绍昨日兵马上万,就算折损不少,也不应该只剩五千,那剩余兵马呢?
“难道是……”管统眼底闪过一丝警觉。
敌军分兵列阵却按兵不动,明显是故意牵制城上守军,让他们把兵力集中在东西两门。
可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为了掩护其他方向的偷袭,还是在调兵?
以曹操的八千兵马,加上袁绍的兵马,至少还有一万七千兵力,攻城还是有实力的。
为什么不来攻城了……难道…是在挖掘地道?
他当即召来亲兵:“去传令,加派哨探巡查城墙四周,在城墙内侧关键位置,挖掘一米深的土坑,将小口大肚的陶瓮、陶罐倒扣在坑底,瓮口朝上,再让听力敏锐的士兵伏在瓮口旁,仔细分辨地下传来的声音。
若敌军在挖地道,铁锹铲土、木锨掘地的震动声会通过土壤传导至瓮李,声音越清晰、越靠近,说明地道离此处越近。
一旦现地下有异动,立刻回报!
再让东西两门守军警惕,切勿被敌军阵型迷惑,只留半数人守城,其余人轮番休整,以防不测!”
亲兵领命而去,管统仍站在城头,脸上淡淡一笑,知道纹丝不动的敌军阵列,这平静之下,藏着袁绍的杀机。
一连三天,袁绍和曹操每日列阵按兵不动,少半天后就收兵回营。
当晚,洛口方向的传令兵急匆匆赶回,带回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历城失手,洛口失手,大公子袁谭和淳于琼都逃往平原郡。
“什么?”袁绍大惊!
斥候探察的消息,历城和洛口的雁门军兵力不足七千人,面对他的一万五千兵马,不战而逃在情理之中。
虽然没有探察到去向,但迹象表明应该是退回东平陵了。
即便是没有退回东平陵,以不足七千兵马,别说是攻击历城的一万兵马了,就是淳于琼五千兵马守卫的洛口,也是难以攻破的。
可现在,洛口丢了,历城丢了!
是什么情况?是什么原因?
不管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两地已经丢了。
这两地一丢,那他的大军就处在了雁门军前后夹击的局面了。
“废物!”袁绍拍着案几,气的大骂。
帐内烛火摇曳,袁绍手指泛白,脸色很快从错愕转为铁青。
“历城、洛口……竟皆失?”他喉间滚出低语,先前胜券在握的锐气瞬间被寒意浇透,心底那丝不安终于凝成了沉疴。
审配见袁绍神色剧变,已知其心已乱,当即上前一步,声音沉稳如磐:“主公,此刻当断则断,撤军为上!
洛口与历城为粮道咽喉,二者皆失,前线无粮可供,粮草一旦紧缺,届时无需敌军来攻,我军自乱。
看来这是赵剑的布局,今雁门军复夺两地,必已布局了攻击我军的后手。
若我军迟疑,一旦赵剑数路来攻,阻断我军退路,恐成瓮中之鳖。”
许攸也赶紧附和:“主公,审公此言有理。我军需避实击虚,保留根本。
今时势已逆,不如暂退平原,凭冀州之地的粮草与兵力重整旗鼓,等待云州有变,赵剑分心之时,再图卷土重来,方为长久之计。”
刘备立于帐侧,见审配和许攸陈词已毕,袁绍面色仍有犹豫,便缓步上前,拱手时姿态谦和,语气更添几分委婉:“明公,正南和子远先生所言,实乃洞见时势之论。
备虽无征战长才,却也略知‘势不可为则退’的道理,愿再为明公进一言。”
他没有直言“撤军”,反而先提旧事,语气带着几分感佩:“昔年明公讨董卓、据冀州,何等雄姿?
正因明公每临大事,从不为一时之困绊住脚步。
今历城、洛口虽失,然冀州根基尚在,将士之心未散。
若为争一时胜负,强留济南,万一粮尽援绝,反折了多年积攒的元气,岂非得不偿失?”
话到此处,他话锋微转,又暗合袁绍心思:“赵剑虽占青州诸地,但平原还在明公手上。明公若此时悄然撤军,避其锋芒,待明公退回平原并重兵扼守,凭冀州粮仓养精蓄锐,再联合曹公和徐州陶公,那时赵剑纵有青州诸地,又怎能与明公的大势抗衡?”
一番话,既不提“退”的窘迫,只论“守势待时”的长远。
既肯定了审配和许攸的建议,又处处捧着袁绍的威望与过往功绩,半句未露催促之意,却让袁绍听来,只觉撤军并非示弱,反是顾全大局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