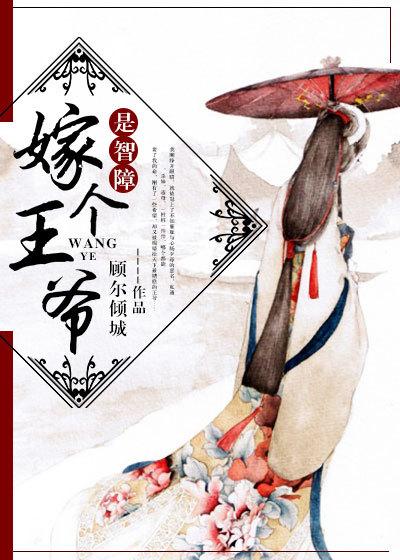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开局上海滩:我以商道破危局 > 第400章 断兰之脉潮信将至(第1页)
第400章 断兰之脉潮信将至(第1页)
青鸟臂弯里的账本"哗啦"滑下两本,他慌忙去接,青布袖口擦过苏若雪膝头时带起一阵风,吹得她手中的碎布条簌簌抖动。"苏小姐,这。。。"他喉结滚动两下,盯着那行"母姓兰,讳芷"的字迹,声音涩,"林芷兰是我义母,断梭会最后一位明面执掌。
二十年前日商要烧尽江南织谱,她带着活谱连夜往松江跑,会里兄弟追去时只看见她的绣鞋漂在黄浦江面。"
苏若雪的指甲掐进掌心,碎布条边缘的毛刺扎得指腹生疼。
她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她的手说"要等",想起母亲的绣袍总带着淡淡艾草香——原来那不是普通的熏香,是织工们防蚕病的法子。
"你母亲没有跳江。"顾承砚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他不知何时立在门框边,月白长衫沾着晨露的湿气,手里捏着本泛黄的《江南织谱》。
见苏若雪抬头,他缓步走近,将书轻轻放在她膝头:"她是潜入地下,把明面的断梭会烧成灰烬,再在暗处重新织网。
而你,"他指尖点过布条上"断梭第七代执灯人"的字迹,又覆上苏若雪冰凉的手背,"是苏家和兰家双脉合一的正统。"
苏若雪的睫毛剧烈颤动。
她翻开《江南织谱》,夹页里突然飘出片碎纸——极细的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兰枝易折,苏根深扎,合则火不灭"几个字像针一样扎进眼里。"这是。。。父亲的批注?"她声音颤,"他早知道母亲的身份?"
"他不仅知道。"顾承砚替她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鬓角,指腹擦过她眼角未干的泪,"当年林芷兰被日商追杀,是你父亲以苏府少东家的身份替她顶了罪,在巡捕房关了三个月。
出来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求苏老爷去林家提亲。"他的拇指摩挲着她腕间的银梭,"苏老爷骂他昏头,他说苏家养蚕,兰家织锦,根脉缠在一起,火才烧不尽。"
青鸟突然单膝跪地。
他腰间的短刀磕在青砖上出脆响,惊得梁上的燕子扑棱棱飞起。"当年义母失踪前,塞给我半块梭形玉佩,说若见苏姓女子持银梭来,便跪。"他从怀里摸出块青玉佩,和苏若雪之前放在香案上的那半块严丝合缝,"苏小姐,断梭会剩下的三百七十二人,都在等这一天。"
苏若雪的银梭突然在掌心烫。
她望着青鸟泛红的眼尾,想起昨夜废墟里千台织机共鸣的轰鸣——原来不是地底下的回声,是断梭会的人藏在瓦砾下,用织机应和她的银梭。
"吴淞口的夜潮,是他们给的投名状。"顾承砚蹲下来与她平视,指节轻轻叩了叩《江南织谱》,"但我们不能急。"他转头看向青鸟,"你想带兄弟去码头探路?"
青鸟喉结动了动:"是。
兰字梭会选在夜潮,必是怕走漏风声。
我带十个兄弟扮作渔户。。。。。。"
"潮声能掩机鸣,也能掩脚步声。"顾承砚打断他,"他们要的不是探查,是确认执灯人。
若派外人去,他们只会当我们是来收编的军阀。"他起身走到窗边,望着院外垂丝海棠在风里摇晃,"若雪,你明日去染坊。"
苏若雪一怔:"染坊?"
"重制鸣蝉机的梭箱。"顾承砚转身时眼里有光,"当年断梭会用潮应机传递信号——潮涨三分,机鸣一声;潮满七分,机鸣三通。
但这机子十年前就被日商烧了。"他从袖中摸出截蚕丝,在指尖绕成小圈,"我让人去丝行挑了最细的冰蚕丝,浸过竹沥水,在特定湿度下会出和潮应机一样的蜂鸣。
你把这弦嵌进梭箱,明日申时三刻,吴淞口的潮声里会多出一声机鸣。"
"他们听得懂?"苏若雪捏着那截蚕丝,掌心的温度让蚕丝微微亮。
"他们等了二十年。"顾承砚替她把蚕丝收进锦囊,"就等这声机鸣,确认执灯人还在。"
青鸟突然起身,把散在地上的账本一本本摞齐。"我这就去染坊备木料。"他走到门口又顿住,回头冲苏若雪笑了笑,"苏小姐,义母当年总说执灯人要像灯芯,烧得越旺,照得越远。
您的眼睛,比她当年还亮。"
门"吱呀"一声合上。
苏若雪望着案头的《江南织谱》,封皮上沾着父亲的墨迹,突然想起昨夜顾承砚说的"带他们走到战火烧不到的地方"。
她摸出银梭,在阳光下,梭身上的水痕竟映出细小的织纹——那是母亲的手,是父亲的字,是断梭会三百七十二双等待的眼睛。
第三日的黄昏来得很快。
苏若雪站在顾宅顶楼,望着西边的火烧云把黄浦江染成金红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