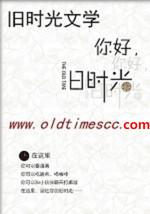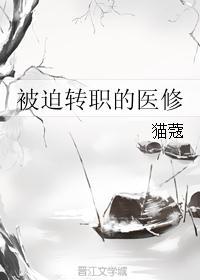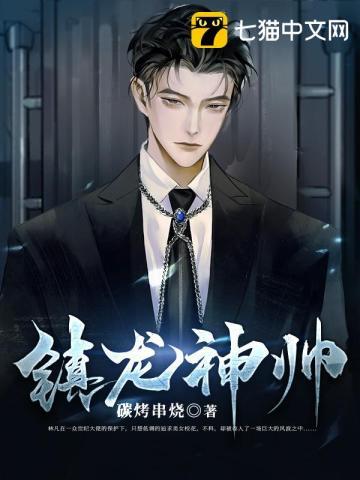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开局上海滩:我以商道破危局 > 第357章 黑箱滴答山本登门(第2页)
第357章 黑箱滴答山本登门(第2页)
是战鼓。
门环叩响的余韵还在青砖缝里打着旋儿,顾承砚的指尖已按上了腰间那枚雕花镇纸——这是方才苏若雪替他别上的,说是"文人也要有个压阵的物件"。
他侧头看苏若雪,她正将《江南织谱》残页往蓝布里裹,动作比往日快了三分,梢却纹丝不乱,像株被风拂过的竹。
"我去。"青鸟的声音从耳后擦过。
他脱了油布雨衣搭在廊柱上,露出里面紧绷的短打,腰间鼓囊囊的——顾承砚知道,那是他藏了三年的勃朗宁。
门闩拉开的瞬间,穿灰布长衫的身影被风卷进来半片。
顾承砚一眼认出是福源米行的陈掌柜,额角还沾着星子雨,手里攥着张皱巴巴的纸条:"顾先生,刚在柜台上拾的,送报的小赤佬说给顾家绸庄的急信。"
苏若雪接过纸条时,顾承砚已瞥见上面的钢笔字:"礼查饭店3o8,今夜子时。"字迹歪扭,像是左手写的,末尾压着半枚樱花纹章。
"山本的请帖。"顾承砚将纸条折成小方块,塞进袖扣暗格里,"他等不及了。"
陈掌柜搓着青灰色袖口:"方才在茶馆听人说,东洋纺织行的伙计满街糖,说顾先生要给山本先生办接风宴。"他浑浊的眼珠突然亮起来,"您昨儿让若雪姑娘递的条子,报馆都登了,现在码头上挑夫都在说东洋人造假!"
顾承砚望着陈掌柜后领上磨破的线头,那是他蹲在米堆里记账时蹭的。
他突然想起现代课堂上,学生们总问"商战的关键是什么",此刻倒有了答案——是这些会在茶馆里嚼舌根的掌柜,会把报纸垫在米筐底的挑夫,是所有被"滴答声"搅得睡不着的普通人。
"陈叔。"他伸手按住对方肩膀,"劳烦您跑趟四马路,把七家商会的当家人都请来。
就说顾某有要紧事相商,戌时三刻,顾家祠堂。"
陈掌柜走时,雨丝已经密了。
苏若雪替顾承砚系好斗篷带子,指尖在他喉结处停了停:"要我跟去码头?"
"你守着织谱。"顾承砚捏了捏她冷的手背,"山本要的是我乱,可我偏要让他看——顾家的账房先生,比绸庄的织机还稳当。"
戌时三刻的祠堂飘着沉水香。
七家商会的当家人挤在长条凳上,茶盏碰得叮当响。
福源米行的陈掌柜、大达轮船的周老板、恒源祥的刘东家。。。。。。顾承砚数了数,连最孤僻的锦云斋绣娘都来了,间别着半朵蔫了的珠花。
"三日后,天蟾舞台。"顾承砚站在祖先牌位前,烛火在他镜片上跳着,"我要请山本谦三当众开那个黑箱。"
周老板的茶盏"当啷"掉在地上。
他是跑长江航运的,嗓门比汽笛还响:"顾少!
那箱子里要是炸弹?
去年虹口纱厂就。。。。。。"
"所以我让青鸟去了法租界。"顾承砚从袖中抽出张纸,是青鸟刚送来的巡捕房回函,"工部局答应派机械师到场,就说可疑爆炸物需专业查验。
山本若真敢放炸子儿,巡捕房第一个掀了他的礼查饭店。"
刘东家捻着山羊胡:"可山本说要归还信物,我们若硬要验,岂不落个疑邻盗斧的名声?"
"他要的就是我们疑。"顾承砚指节敲了敲供桌,"这半个月,全上海的耳朵都被那滴答声攥着——听声不如见物,见物不如验心。
等他开了箱子,是真归还还是作秀,一目了然。"
众人交头接耳时,顾承砚瞥见陈掌柜在桌下给锦云斋绣娘使眼色。
那绣娘突然站起,珠花颤得厉害:"顾先生,我信你。
当年我男人被东洋布庄挤得跳黄浦江,是您父亲送了十车蚕丝,说绣娘的针脚,比黄金金贵。"她抹了把眼睛,"今儿您说开箱子,我锦云斋出五十个绣娘,把舞台围得水泄不通!"
祠堂里突然静了。
周老板弯腰捡起茶盏,往地上一磕:"我大达轮船调三艘汽艇,把外滩的记者都接来!"陈掌柜拍着胸脯:"福源米行出两百口袋米,给守夜的百姓当宵夜!"
顾承砚望着这些被生活磨得粗糙的脸,突然想起穿越前夜,他在图书馆翻到的《上海工商志》——上面写着"民国廿五年,顾氏绸庄联合七商,以织印为旗,破东洋诡计"。
原来史书上的浓墨重彩,不过是眼前这些人,愿意为一句"信你",把家底都掏出来。
仪式前夜的顾家密室飘着墨香。
苏若雪跪坐在蒲团上,面前摊开《江南织谱》残页,旁边是父亲临终前写的"雪儿勤学"手札。
她的指尖在残页"出锋七分"的笔锋上反复摩挲,又移到手札的"勤"字——那个"力"部的回锋顿笔,竟和残页里"织"字的尾笔,像同一个模子刻的。
"父亲。。。。。。"她喉咙紧,从妆匣里摸出枚铜顶针,那是父亲教她打算盘时套在食指上的,"您总说假作真时真亦假,难道这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