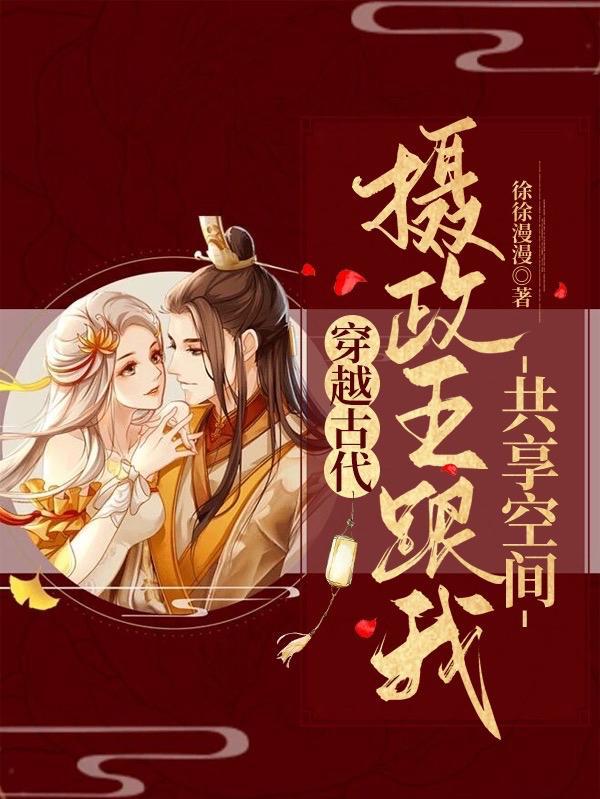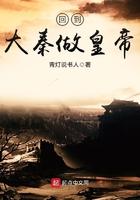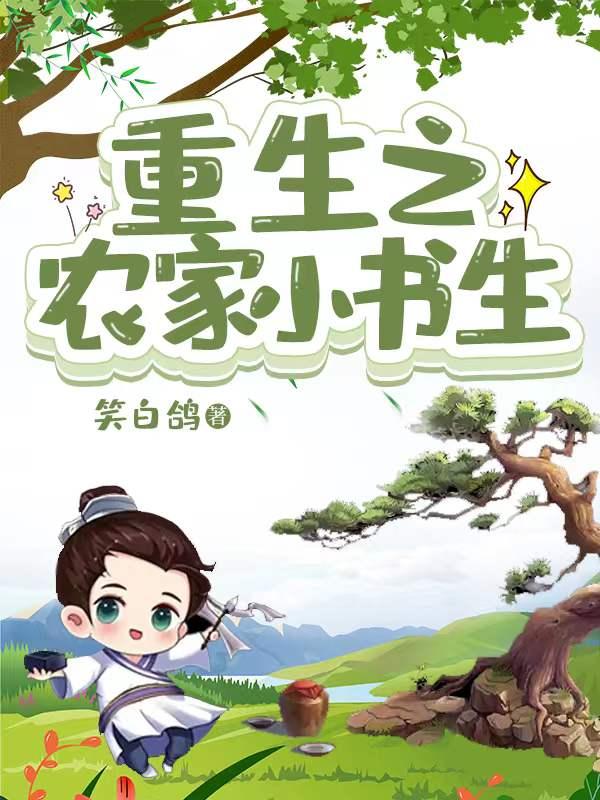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核废土上崛起 > 第379章 风不送信只推人往前(第1页)
第379章 风不送信只推人往前(第1页)
那风声仿佛有了实体,钻入苏瑶女儿安安的梦中,化作冰冷的触手。
小女孩在深夜猛地坐起,瞳孔里映着窗外的月色,却空洞得像两口深井。
“妈妈,”她的声音带着哭腔,小手紧紧抓着苏瑶的胳膊,“字在爬,它们又在爬了,顺着我的腿往上爬!”
苏瑶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她抱住瑟瑟抖的女儿,目光却投向了床头柜上那份刚刚拿到的体检报告。
医学组的专家们围着那张脑电波图谱,脸上的震惊和困惑挥之不去。
安安的脑电波,在梦呓时呈现出一种匪夷所思的规律性,其频率,与高空风语监测站捕捉到的主频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七的高度同步。
“前所未有的神经共振现象,”医学组组长陈博士推了推眼镜,语气凝重,“我们无法解释其原理,但风险不可估量。为了孩子的安全,也为了防止这种‘共振’扩散,我们建议立即进行隔离观察。”
隔离。
这个词像一枚钢针刺进苏瑶的耳膜。
她看着怀里渐渐平复下来,却依旧眉头紧锁的女儿,一个疯狂的念头压倒了所有的理智与恐惧。
她不相信这是一种病。
如果风在说话,而她的女儿是唯一能听见的人,那她要做的不是隔绝,而是靠近源头。
凌晨四点,苏瑶没有签署隔离同意书,而是用毯子裹紧安安,悄悄离开了住所。
她抱着女儿,穿过寂静的街道,最终停在了城市中心广场那棵巨大的老槐树下。
这是她和许墨定情的地方,是这座金属城市里,为数不多还保留着泥土气息的圣地。
她将安安轻轻放下,自己则跪倒在地,将耳朵紧紧贴在粗糙冰冷的树干上。
风吹过树冠,出沙沙的声响,像无数细碎的耳语。
安安似乎受到了某种感召,也学着妈妈的样子,将小小的耳朵贴在了另一侧的树干上。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就在苏瑶几乎要放弃的时候,一种极其微弱、却极富节奏感的声音,从树心深处传来,穿透厚厚的木质,敲击在她的耳廓上。
咚。咚咚。咚。
不是心跳,不是虫蛀。
那是一种规律的、人为的敲击声。
苏瑶屏住呼吸,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她对这个节奏太过熟悉,在通讯还未如此达的年代,许墨曾手把手教过她。
是摩斯电码。
她闭上眼,在脑海中飞翻译着那来自树心的密语。
一个又一个数字浮现,最终组成了一串她刻骨铭心的序列——她丈夫,许墨的生日。
一瞬间,泪水决堤。
苏瑶猛地抱住女儿,在她耳边用颤抖却无比坚定的声音说:“安安不怕,爸爸在跟我们说话。”
第二天,苏瑶当着所有医学专家的面,撕毁了隔离观察的建议书。
她拒绝了所有干预性治疗方案,反而从生态舱领回一大捆柔韧的藤条。
她花了一整天的时间,为安安编了一顶漂亮的藤编帽,又将她珍藏的、许墨留下的几枚碎晶尘小心翼翼地缝入帽子内衬。
“你们想把她当病人,”苏瑶为女儿戴上帽子,眼神锐利如刀,扫过众人,“但我决定,如果她真的能听懂风,那就让她成为这个世界的第一代‘步行译者’。”
与此同时,在地下生态舱的最深处,林小雨正对着一张巨大的迁徙地图一筹莫展。
地图的最后一段戛然而止,像一条被斩断的生命线。
所有的地质勘探数据都显示,前方是无尽的戈壁,再无任何水源。
她的目光烦躁地扫过生态舱内繁茂的植物,那些藤蔓绿得几乎不真实。
许墨曾开玩笑说,植物是地球最早的诗人,把故事呼进大气里。
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划过她的脑海。
呼吸。蒸腾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