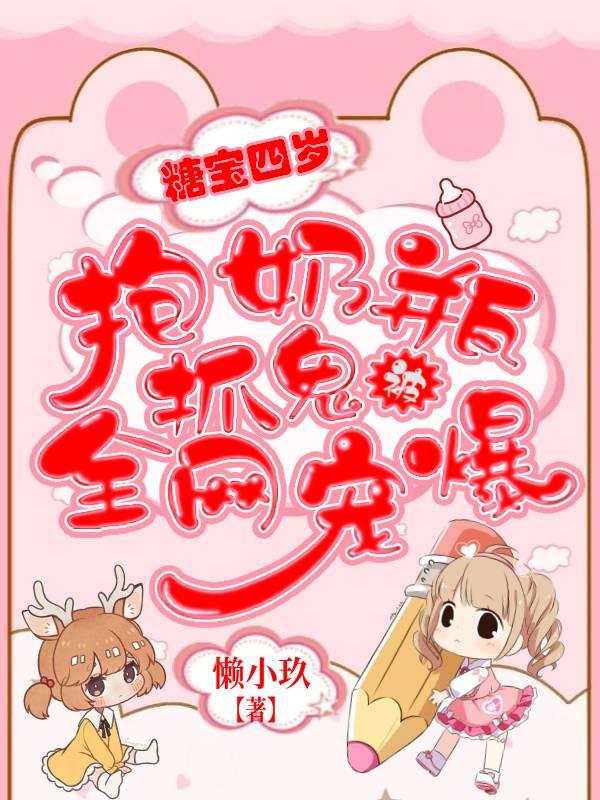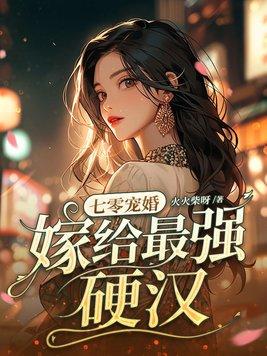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核废土上崛起 > 第354章 讲到一半的课(第1页)
第354章 讲到一半的课(第1页)
北境的风像一把生锈的钝刀,刮过废弃雷达阵列时,带起一片令人牙酸的呜咽。
林小雨的队伍在阵列下的避风处扎营,篝火驱散了严寒,却驱不散那仿佛来自地狱深处的规律嗡鸣。
队员们裹紧了毯子,试图用闲聊抵御这诡异的声音,但林小雨却皱起了眉。
她不是第一次在野外听见风声,但这一次,声音里有一种不属于自然的秩序感。
她取出了随身携带的音频分析仪,将探头对准了那座最高、断裂最严重的天线。
设备屏幕上,杂乱的波形中,一条微弱但极其稳定的信号顽固地跳动着。
她戴上耳机,指尖在虚拟键盘上飞敲击,过滤,降噪,放大。
嗡鸣声在她的耳中逐渐变得清晰,分解成无数细碎的数据流。
几分钟后,当最终的分析结果呈现在屏幕上时,林小雨的呼吸骤然停止。
那不是噪音,而是一幅被编码成声波的地质剖面图。
图谱的结构清晰得可怕,精准地标注出地下三百米处一条从未被勘探记录过的庞大含水层。
这正是他们此行的目标。
然而,在剖面图最下方的标注点旁,一行用不同频率编码的小字,像一个冰冷的纹身,烙印在数据流的末尾。
“别钻太深,会吵醒老脉冲。”
林小雨的血液仿佛瞬间凝固。
这轻佻中带着一丝警告的语气,这把地质活动称为“脉冲”的习惯——整个“声纹墙”计划里,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
许墨。
但这个数据,这份由风声传递的图谱,却从未在“声纹墙”的任何数据库中出现过。
它就像一个来自坟墓的幽灵,在旷野的风中对她低语。
信号被以最高加密等级传回了中央控制室。
苏瑶看着屏幕上那段来自北境风声的数据,脸色比窗外的夜色还要凝重。
她的手指在控制台上划过,调出系统深处一个被她标记为“异常”的档案库。
这里存放着近十年来所有无法解释的、却又被证明无比正确的“知识碎片”。
从一种全新的抗寒作物基因序列,到一次精准预测的太阳风暴,它们的出现方式五花八门,有时是某个孩童无意的哼唱,有时是一段边远地区流传的民谣。
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带着许墨那独有的、仿佛洞悉一切的风格。
她将林小雨现的新数据作为关键节点导入系统,命令级计算机重新进行溯源分析。
她怀疑的不是信息的真伪,而是其传递的方式。
这不是简单的教学,更像是一种……干预。
每一次,“许墨式”的知识都精准地出现在人类群体认知即将陷入瓶颈或走向错误方向的前夜,像一只无形的手,在最关键的时刻轻轻推了一把。
几小时后,一张巨大的全息图在控制室中央展开。
那是一棵倒置的、由无数光点和线路构成的巨树。
它的树冠覆盖全球,每一条枝丫都连接着一个或大或小的认知突破事件。
而所有枝丫,无论多么繁茂,最终都汇向同一个根系。
那根系深深扎在一个坐标点上,系统将其标记为——“第一声源”。
苏瑶怔怔地看着那棵光的树,指尖冰凉。
她终于明白了。
许墨不是在讲课,也不是在传递信息。
他是在用自己的知识和存在,为这个濒临崩溃的文明,嫁接一条全新的、能够自我修复和进化的神经系统。
而此刻,那个“神经系统”的缔造者,正站在无垠的冰原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