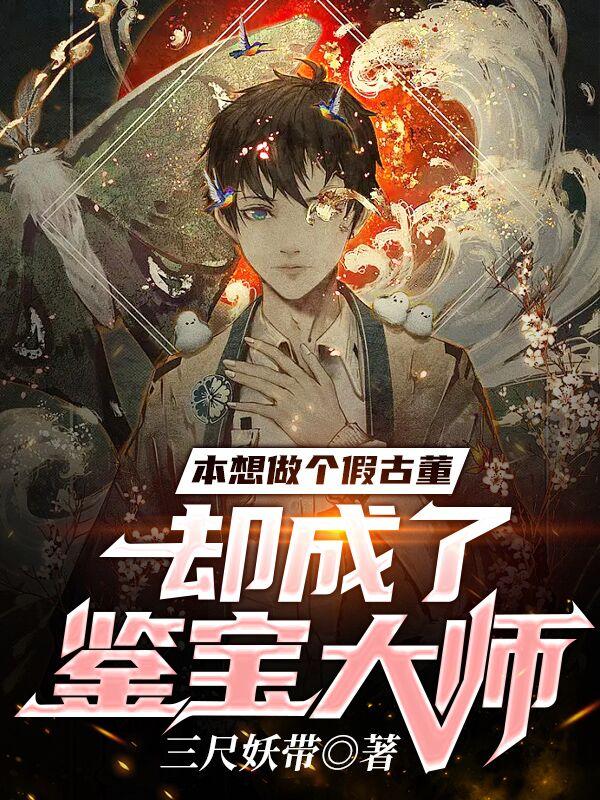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核废土上崛起 > 第347章 破电台不响但沙子会写信(第1页)
第347章 破电台不响但沙子会写信(第1页)
这片黑暗并非源于绝望,而是来自未知。
它像一块巨大的磁铁,牢牢吸附住吴海的全部心神。
他迫切需要一个支点,一个能撬动这片沉重迷雾的支点。
他的目光最终落在了吴老临终前交给他那块粗糙的沙岩片上。
那东西一直被他贴身收藏,触感冰冷,仿佛还残留着极地的寒意。
岩片不大,刚好能握满掌心,表面布满了细密得如同蛛网的划痕,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言。
整个第五营地的专家都曾试图解读它,有人说这是某种失传的象形文字,有人认为是星图,但所有的猜测都在一次次失败的破译中被推翻。
它成了一份无法被阅读的遗书,一个沉默的谜题。
吴海将岩片带到了x-819的分析中枢。
冰冷的蓝色光束在岩片表面缓缓扫过,将每一道刻痕的深度、宽度、角度都转化为精确到微米的数据。
显示屏上,三维模型旋转着,那些杂乱的划痕在x-819的算力下被拆解、重组,却依旧呈现为一堆无意义的乱码。
“信息熵过高,无法识别为任何已知编码体系。”x-819的合成语音一如既往的平稳。
“再试一次,”吴海的声音有些沙哑,他死死盯着屏幕,脑中回响着那段神秘的口琴声,“把环境因素加进去。风,极地的风。”
这是一个疯狂的念头,近乎于直觉。
x-819沉默了片刻,似乎在评估这个指令的逻辑性。
随即,新的模拟程序启动。
虚拟风洞在数据世界中生成,风从微风到烈风,逐级递增。
当风被设定在一个特定的临界值时,奇迹生了。
那些深浅不一的刻痕,在虚拟气流的冲击下,开始产生不同频率的微弱振动。
就像一排长短不一的笛管,高低音此起彼伏。
x-819强大的音频处理器将这些振动捕捉、放大、组合,一段断断续续、夹杂着风声的语音被还原了出来。
那是一个年轻而坚定的男声,充满了不羁的狂想。
“……他们以为沙子是死的,只会屈服于风。但他们错了。只要刻下正确的痕迹,风就会成为信使,成为歌者……总有一天,我会让风替我说话。”
是许墨。
整个分析中枢寂静无声,只有那段独白的回音仿佛还在空气中震荡。
吴海浑身一颤,终于明白了。
这不是文字,这是声音的化石。
吴老留下的不是遗书,而是一把钥匙,一把开启全新通讯维度的钥匙。
这种匪夷所思的编码方式,他将其命名为——“风蚀编码”。
灵感的火花一旦点燃,便迅燎原。
吴海召集了营地里最顶尖的机械师和程序员,他要将这个被动的编码方式,变成一种主动的表达工具。
他要造一台机器,一台能将语音直接转化为沙地微刻的便携装置。
他称之为“沙写机”。
半个月后,第一台原型机被推上了测试场。
它像一只笨重的金属甲虫,底部伸出数十根高频振动的探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