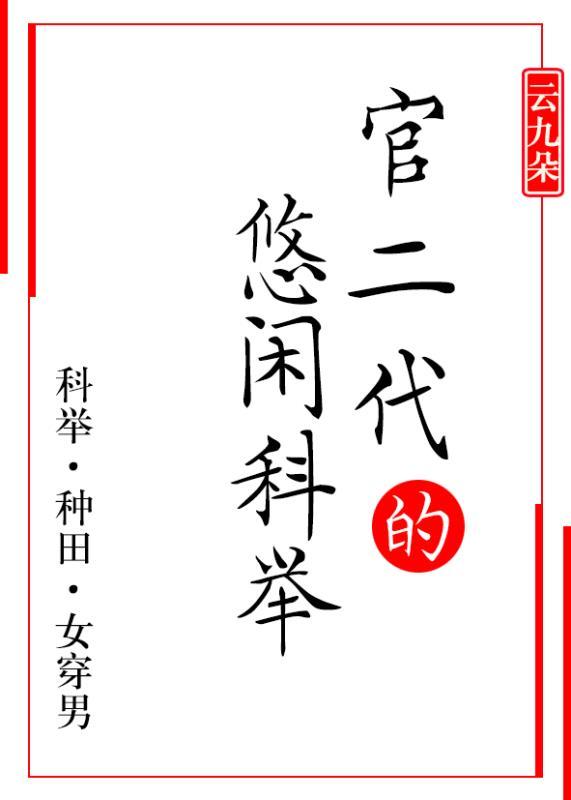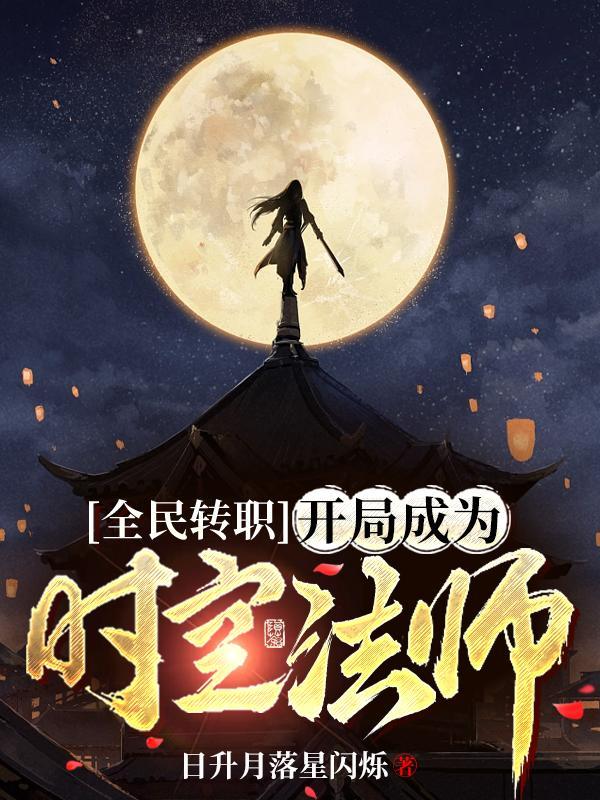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了解历史之大汉王朝 > 第1章 汴梁雪夜 龙椅下的刀光与囚笼里的诗魂(第1页)
第1章 汴梁雪夜 龙椅下的刀光与囚笼里的诗魂(第1页)
一、紫宸殿的烛影与北伐心
大宋开宝九年冬,汴梁城的雪下得比往年都要早。鹅毛般的雪片从铅灰色的天空里簌簌落下,不到半个时辰,就把皇城根下的朱红宫墙染成了素白,连紫宸殿檐角那几只镇脊的铜兽,都裹上了一层薄薄的雪绒,活像被冻住了的巨兽,耷拉着脑袋瞅着底下往来的宫娥太监。
殿内却暖得很。地龙烧得正旺,空气中飘着龙涎香的醇厚气味,混着案头鎏金铜炉里燃着的沉香,暖融融地裹在人身上。赵光义穿着一身赭黄绣龙常服,正背着手在殿内来回踱步,玄色的靴底踩在铺着的波斯地毯上,没出半点声响——可那股子压不住的焦躁,却像殿外的寒气似的,顺着门缝往殿里钻,连站在一旁的内侍都忍不住缩了缩脖子,把手里捧着的茶盏端得更稳了些。
他刚登基不过三个月。太祖赵匡胤那事儿,到现在还像根刺似的扎在朝野上下每个人心里。虽说对外只说是“太祖偶感风寒,猝然崩逝”,可京城里私下传得沸沸扬扬的“烛影斧声”,他不是没听见。前些天去国子监视察,见着几个老儒凑在一块儿嘀咕,见了他过来就立马闭了嘴,那眼神里的探究和怀疑,跟针似的扎得他后背紧。
“陛下,赵相公到了。”内侍尖细的嗓音打破了殿内的沉默,也把赵光义从杂乱的思绪里拉了回来。
“让他进来。”赵光义转过身,快步走回龙椅旁,伸手理了理衣襟上的龙纹,努力让自己的表情看起来沉稳些——可那微微蹙着的眉头,还是泄了气。
门帘被轻轻掀开,一股寒气裹着雪粒子钻了进来,紧接着,一个穿着藏青色宰相袍的身影走了进来。赵普今年已近六十,头花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深得能夹死蚊子,可走起路来依旧腰杆挺直,只是那双往日里总是透着精明的眼睛,此刻多了几分审慎。他刚踏进门,就把沾了雪的官帽摘下来,递给身后跟着的小吏,又拍了拍袍角上的雪沫子,这才上前几步,躬身行礼:“臣赵普,叩见陛下。陛下圣安。”
“起来吧。”赵光义指了指旁边的紫檀木椅,“赐座。李德全,给赵相公倒杯热茶,要刚煮好的祁门红茶。”
“谢陛下。”赵普谢了恩,小心翼翼地在椅子上坐了半边屁股,双手放在膝盖上,腰杆依旧挺得笔直——他跟了太祖大半辈子,如今换了新帝,虽说赵光义当年也算是他看着长大的,可君臣有别,该守的规矩半点不能差。
李德全麻利地倒了杯茶,双手捧着递到赵普面前。赵普接过茶盏,指尖触到温热的杯壁,心里才稍稍松了些。他低头吹了吹茶面上的浮沫,眼角的余光却悄悄瞥了一眼坐在龙椅上的赵光义——这位新帝,比太祖性子急多了,也沉不住气多了。
果然,没等赵普把茶喝下去,赵光义就先开了口:“赵相公,朕今日叫你来,是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如今朕登基也有些时日了,朝堂上虽说还算安稳,可朕总觉得,底下人看朕的眼神,不太对。”他顿了顿,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龙椅扶手上的雕纹,“你也知道,太祖皇帝威望深重,当年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平定四方,那是实打实的功绩。朕呢?朕虽说也跟着太祖南征北战,可终究没做出过什么能让天下人信服的大事。”
这话算是说到了赵普心坎里。他放下茶盏,抬头看向赵光义,语气恭敬却不谄媚:“陛下言重了。陛下当年随太祖皇帝平定李重进、征讨北汉,战功赫赫,朝中诸将哪个不敬佩?只是太祖皇帝刚崩,人心难免有个适应的过程,陛下不必过于焦虑。”
“焦虑?朕能不焦虑吗?”赵光义猛地提高了声音,手指在扶手上重重一敲,“前些天吏部尚书张昭,在朝堂上跟朕奏事,话里话外都在提‘太祖旧制’,朕说要改一改江南漕运的规矩,他立马就说‘太祖当年定下的规矩,轻易动不得’——他这是把朕当什么了?当摆设吗?还有那些地方上的节度使,虽说都上表称臣了,可谁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万一哪天有人借着‘烛影斧声’的由头起兵,朕该怎么办?”
赵普心里暗暗叹气。他就知道赵光义会提这些。太祖崩得突然,赵光义登基虽说是“金匮之盟”为依据,可那“金匮之盟”是当年杜太后定下的,太祖活着的时候没往外说,如今突然拿出来,难免让人觉得有猫腻。更何况,赵光义登基后,先是把弟弟赵廷美封为开封尹,又把太祖的儿子赵德昭、赵德芳加官进爵,看似是顾念亲情,实则是怕人说他刻薄宗室——可越是这样,越显得他心里虚。
“陛下,张尚书此举,并非是不敬陛下,只是老臣心思,总想着遵循旧制以求安稳。”赵普放缓了语气,尽量让自己的话听起来更中肯些,“至于地方节度使,陛下登基后已经减免了江南三州的赋税,又派了转运使去各地巡查,安抚百姓,他们就算有心思,也不敢轻易动——毕竟,谁也不想跟安稳日子过不去。”
“安稳日子?”赵光义冷笑一声,站起身走到殿中,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赵相公,你跟着太祖皇帝这么多年,该知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道理。朕要的不是‘暂时安稳’,是‘长治久安’!是让天下人都知道,朕赵光义,配坐这龙椅!配当这大宋的皇帝!”
他猛地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向赵普:“你跟朕说,朕要怎么做,才能让天下人信服?才能让那些嚼舌根的人闭嘴?”
赵普沉吟了片刻。他知道,赵光义要的不是安抚,是一个能让他立威的机会。太祖当年靠什么立威?靠打仗,靠平定天下。如今南方已定,剩下的,就只有北边的契丹和那片让太祖到死都没能收回来的幽云十六州了。
想到这儿,赵普抬起头,眼神也变得坚定起来:“陛下,臣倒有一计——完成太祖皇帝未竟的事业,北伐契丹,收复幽云十六州!”
“幽云十六州?”赵光义的眼睛一下子亮了。他怎么会忘了这个?当年太祖皇帝在宫里专门设了个“封桩库”,说是要攒够钱,要么买回来,要么打下来,可直到太祖崩了,那库银攒了不少,幽云却还是在契丹人手里。这些年,他每次想起这事,都觉得心里堵得慌——要是他能把幽云收回来,那可比太祖厉害多了!
“对,就是幽云十六州!”赵普加重了语气,“太祖皇帝在位时,多次想北伐,可那时候南方还有南唐、吴越、南汉这些割据势力,腹背受敌,只能暂且搁置。如今陛下圣明,南方已定,天下一统,正是北伐的好时机!陛下若能亲率大军,北上征讨契丹,把幽云十六州收回来,让那些被契丹人奴役的汉人重归大宋,到时候,不仅朝中大臣会敬佩陛下,天下百姓也会感念陛下的恩德,谁还敢说陛下不配坐这龙椅?谁还敢提那些无稽之谈?”
赵光义听得心潮澎湃,忍不住在殿里来回走了好几圈,双手握拳,脸上满是兴奋:“好!说得好!赵相公,你这话说到朕心坎里去了!朕早就想做件比太祖更伟大的事,收复幽云,正是最好的机会!”他停下脚步,看向赵普,语气斩钉截铁,“明日早朝,朕就下旨,召集将领,商议北伐之事!”
可兴奋劲儿过了,他又想起了现实问题,眉头微微皱了起来:“只是,北伐不是小事。契丹兵力强盛,这些年在幽云经营多年,城防坚固,咱们要打过去,得有足够的粮草和兵力。粮草还好说,封桩库里有太祖攒下的银子,再从江南调些粮食过来,应该能撑一阵子。可兵力……如今禁军虽说有二十多万,可分散在各地驻守,能抽调出来北伐的,怕是不多。还有将领,太祖当年的老部下,像石守信、高怀德他们,虽说还在朝中,可年纪也大了,能不能打仗还不好说。”
赵普早就想到了这些,他从容地回答:“陛下放心,兵力的事,臣已经有了初步的打算。禁军里有三万‘骁胜军’,都是这些年挑选出来的精锐,战斗力极强,可先行调往河北边境驻扎,作为先锋。再从陕西、河东调五万边军,补充兵力,这样主力部队就有八万多人。至于将领,石守信、高怀德虽老,可经验丰富,可任命为副将,辅佐陛下。另外,禁军殿前司都虞候崔翰,年轻有为,勇猛善战,去年征讨北汉时立了大功,可任先锋大将。还有彰德军节度使李汉琼,熟悉契丹军情,可任随军参谋——有这些人辅佐陛下,北伐之事,胜算不小。”
赵光义听着,不住地点头,脸上的愁云渐渐散去:“好!有赵相公你费心筹划,朕就放心了!粮草和兵力的事,就劳烦你多盯着点,有什么需要朕出面的,随时跟朕说。”
“臣遵旨!”赵普站起身,再次躬身行礼,“陛下放心,臣定当尽心竭力,辅佐陛下完成北伐大业,收复幽云,告慰太祖皇帝在天之灵!”
赵光义满意地点了点头,挥了挥手:“行了,你先下去吧。明日早朝,朕等着你的奏疏。”
“臣告退。”赵普又行了一礼,转身慢慢退出了紫宸殿。
刚走出殿门,一股寒风扑面而来,带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冰凉刺骨。赵普裹紧了身上的宰相袍,抬头看了看漫天飞雪的天空,轻轻叹了口气。他刚才在殿里说得慷慨激昂,可心里却清楚得很——赵光义急于北伐,哪里是只为了立威?更重要的是,他想摆脱“烛影斧声”的阴影,想用一场大胜来堵住所有人的嘴。可契丹人不是软柿子,当年太祖皇帝那么厉害,都没敢轻易动手,赵光义性子急,又没怎么单独指挥过大规模的战役,这场北伐,怕是不会那么顺利。
他回头看了一眼紫宸殿那扇紧闭的门,心里暗暗嘀咕:陛下啊陛下,你这步棋,走得太急了。可事到如今,他作为宰相,也只能跟着走下去——毕竟,大宋的安危,比什么都重要。
与此同时,汴梁城西南角的违命侯府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侯府不大,原本是前朝一个官员的旧宅,后来太祖灭了南唐,把李煜掳到汴梁,就把这宅子赏给了他,还封了个“违命侯”的爵位——说是爵位,其实跟软禁也没什么区别。门口常年站着两个禁军士兵,府里的丫鬟太监,也都是宫里派来的,明着是伺候,暗着其实是监视。
此刻,李煜正坐在书房的窗前,手里拿着一本《昭明文选》,可眼睛却没看在书上,而是直直地盯着窗外院子里的积雪。他穿着一身素色的锦袍,头用一根玉簪松松地挽着,脸色苍白,下巴上留着淡淡的胡须,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苍老些。自从去年被掳到汴梁,他就没怎么笑过,那双往日里总是透着书卷气的眼睛,如今满是愁苦和落寞。
“官家,该喝药了。”一个穿着青绿色丫鬟服的小丫鬟端着一碗黑漆漆的汤药走了进来,轻声说道。这丫鬟叫春桃,是宫里派来的,性子还算温顺,不像其他几个太监那样尖酸刻薄。
李煜没有回头,只是摆了摆手,声音沙哑:“放那儿吧。”
春桃把药碗放在书桌一角,看着李煜落寞的背影,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说道:“官家,这药是太医开的,说是能驱寒,您还是趁热喝了吧。外面雪下得这么大,仔细着凉。”
李煜依旧没动,只是喃喃地说道:“着凉?我如今这样,着凉又能怎么样?死了,倒也干净。”
“官家!”春桃吓了一跳,连忙上前一步,压低声音说道,“您可不能说这话!要是被外面的人听见了,传到宫里去,可就麻烦了!”
李煜苦笑一声,转过头看向春桃:“麻烦?我如今还有什么麻烦可怕的?亡国之君,阶下之囚,连自己的故国都回不去,活着跟死了,又有什么区别?”
春桃被他说得眼圈泛红,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知道李煜心里苦,也知道他想念南唐,可她只是个小丫鬟,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轻轻叹了口气,退到一旁,默默地收拾着桌上的杂物。
就在这时,书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一个穿着粉色襦裙的女子走了进来。女子身姿窈窕,面容娇美,只是脸色也有些苍白,眉宇间带着几分忧愁——正是李煜的皇后,小周后。
“娥皇……”李煜看到小周后,眼神里才多了几分暖意,连忙站起身,上前几步,握住她的手,“外面雪这么大,你怎么过来了?仔细冻着。”
小周后摇了摇头,反手握住李煜的手,轻声说道:“我在房里待着,总觉得心里不踏实,过来看看你。”她看了一眼桌上的药碗,又看了看李煜苍白的脸色,忍不住皱起眉头,“你又没喝药?太医说你身子弱,得按时喝药才行。”
李煜低下头,不敢看她的眼睛:“我不想喝,那药太苦了。”
“苦也得喝!”小周后故作严肃地说道,可语气里满是心疼,“你要是倒下了,我怎么办?咱们如今虽说过得苦,可只要你好好的,我就不怕。”
李煜听着,心里一阵愧疚。他知道小周后跟着他受了太多苦。当年在南唐,她是备受宠爱的皇后,锦衣玉食,万人敬仰,可如今跟着他来到汴梁,不仅要忍受囚禁之苦,还要处处看人脸色,甚至连出门都要报备。他轻轻把小周后搂进怀里,声音哽咽:“娥皇,委屈你了。跟着我,让你受了这么多苦。”
小周后靠在他怀里,眼圈也红了,可还是强忍着眼泪,轻轻拍了拍他的背:“陛下,别这么说。当年在金陵,你对我那么好,如今就算过得苦些,我也心甘情愿。咱们是夫妻,本该同甘共苦。”
她从李煜怀里抬起头,擦了擦眼角的泪水,轻声说道:“对了,刚才我听府里的老太监说,太祖皇帝驾崩的消息,已经传遍汴梁了。新帝赵光义,已经登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