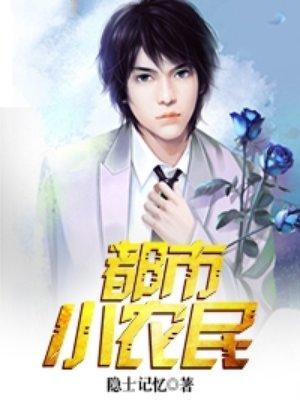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乞族 > 第755章 飞头行军(第2页)
第755章 飞头行军(第2页)
眼前的景象豁然开朗。
一片相对开阔的腐潭边缘,火光跳跃——并非篝火,而是几盏用沼犀油脂和光苔藓混合点燃的简陋石灯,散着昏黄而腥臭的光芒。
阿花的猎手营六百余人正在这里忙碌着。
他们几乎人人都成了泥人,身上、脸上糊满了黑绿色的恶臭淤泥,汗水冲出一道道沟壑,但每个人的眼神却都亮得吓人,充满了一种原始而暴烈的兴奋。
地上,已然躺着十几头如同小山般的庞然大物——正是那种皮糙肉厚、性情狂暴的“沼犀”!
这些巨兽皮肤如同覆盖着厚厚的、布满瘤节的青黑色岩石,粗糙无比,此刻却已被开膛破肚,暗红色的鲜血染红了大地,浓烈的血腥味和内脏的腥气几乎令人作呕。
猎手们三人一组,五人一队,正用尽各种手段对付这些巨兽。
有人手持顶端绑着巨大燧石片的粗木长矛,冒着被踩扁的风险,疯狂地捅刺沼犀相对脆弱的眼睛、鼻孔和腹部;有人则甩出浸过水的、异常坚韧的藤索,试图绊倒这些庞然大物;更多的人,则是在巨兽被放倒后,一拥而上,用骨刀、石斧疯狂地切割着那厚韧无比的兽皮!
“嘿——哟!嘿——哟!”
粗犷的号子声响起,几十名壮汉正喊着号子,用削尖的硬木杠,费力地将一张刚刚从沼犀身上剥下、还滴淌着粘稠血液和脂肪的巨大兽皮抬起,重重扔进旁边一个早已挖好的、灌满了浑浊粘稠液体的大坑里。
那坑中液体散着强烈的酸涩和怪异的草药味,是用来初步鞣制兽皮的“药池”。
另一边,一些手脚麻利的妇人和老匠人,正用磨尖的骨针和浸过油的兽筋,将一些较小的、或是处理好的皮块飞快地缝合在一起,试图拼凑出更大的皮囊。
空气中回荡着皮索拉扯的吱嘎声和骨针穿透皮膜的闷响。
整个场面混乱、血腥、野蛮,却又充满了一种热火朝天的、为生存而战的蓬勃力量。
“快!这边!这张皮子够厚实!多泡一会儿!”
“缝合处勒紧!对!用死结!要是漏水,老子扒了你的皮!”
阿花站在一处稍高的土坡上,吊着的胳膊似乎已无大碍,她单手叉腰,声音嘶哑却洪亮,
如同指挥一场大战的女战神,脸上溅满了泥点和血污,眼神却锐利如刀,不断扫视着全场,出各种指令。
听到阿花集合的声音,这群刚刚经历了一场“狩猎”盛宴的猎手们,虽然疲惫,却都兴奋地嗷嗷叫起来,迅向着她所在的位置靠拢。
他们看着彼此身上的血污和淤泥,非但不觉得狼狈,反而出粗野的笑声,互相捶打着胸膛,展示着今日的“收获”。
就在这时,子辉骑着大黑,带着那片无声悬浮的死亡阴云(飞头队)和木梭等人,如同暗夜中浮现的鬼魅,悄然出现在了营地的边缘。
兴奋的喧嚣瞬间一滞。
所有猎手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和笑闹,目光齐刷刷地投向那突兀出现的队伍,尤其是看到族长亲至,以及那片令人头皮麻的悬浮飞头时,眼神中不由得带上了一丝敬畏和惊疑。
阿花也是一愣,随即大步迎了上来,蜡黄的脸上带着疑惑:“族长?你怎么来了?还带了。。。这么多‘飞头’?”
她的目光扫过那些沉默的无头身躯和空中的飞头,即使是她,也觉得这景象有些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