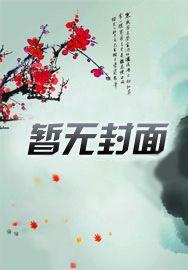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三国凶兵:我为汉室续命八百年 > 昆哥和大家聊聊天(第1页)
昆哥和大家聊聊天(第1页)
朔日大朝会的喧嚣余音尚未在长安城上空完全消散,那场“三请三辞”最终晋位唐王的盛大典礼的华彩仍萦绕在朱墙金瓦之间。晋位唐王后的刘昆,并未如外界揣测那般居于新赐的、尚在修缮的宏丽王府,而是依旧驻跸于原本的大将军府内正殿——这里的一砖一瓦更令他感到踏实,也更能向外界昭示其重实轻华的执政之风。
殿内,沉香细烟自兽炉中袅袅升起,却驱不散弥漫在空气中的凝重。与会者皆为刘昆集团的核心班底:左仆射戏志才、户部尚书黄玄、御史大夫华歆、礼部尚书刘岱、刑部尚书卢植,以及军方代表、刚刚奉命从广陵快马赶回,征尘未洗的高顺。他们分列两侧,人人面色肃然,等待着王座上的那位开口。
刘昆端坐于主位之上,身着一袭玄色王袍,金线绣制的蟠龙纹路在烛光下若隐若现,仿佛随时欲破衣而出。历经传国玉玺的洗礼与臻至八倍“叠劲”的至高境界,他周身自然流露出一股渊渟岳峙、不怒自威的气度。他目光沉静,缓缓扫过麾下这些文武重臣,并未因新晋王爵而有丝毫得意,反而眉宇间凝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
“诸公,”刘昆的声音平稳而有力,打破了殿内的寂静,“孤蒙陛下错爱,百官推举,暂领唐王之位,然天下未靖,百废待兴,实非论功行赏、安享尊荣之时。今日召诸公前来,非为虚礼,乃欲听实话,知实情,议实事。左仆射,就从朝廷这半年来的动向说起吧。”
被率先点名的戏志才应声出列。他身形清瘦,面容因常年殚精竭虑而略显苍白,但一双眼睛却锐利如鹰,仿佛能洞穿一切迷雾。他手持一卷文书,微微躬身,语不疾不徐,却字字清晰:“启禀唐王。自五月王师东征,至十一月凯旋,这半年间,长安朝局大体平稳,然水下亦有暗流。”他略一停顿,继续道,“朝中大臣,尤其如太傅马日磾、太尉杨彪、卫尉士孙瑞等前朝老臣,自大将军奉玉玺归朝、天显异象之后,其态度颇有转变。彼等昔日虽心向汉室,常怀忧虑,然那日异星耀空、帝星黯淡之象,彼等亦亲眼目睹,对其冲击甚大。”
戏志才微微抬头,观察了一下刘昆的神色,见其面无表情,便接着说:“马日磾公近日称病,深居简出,府门紧闭,谢绝访客。据探,其于府中时常独坐叹息,曾对家人言‘天意渺茫,非人力可违’,似有心灰意懒之态。杨彪公则依旧每日上朝,然于朝堂之上沉默寡言,以往常就典章制度、先帝旧事与王司徒(王允)争辩,如今皆不复见。其子杨修,近日活动反倒更为频繁,与清流学子交往甚密,言论间对唐王颇多揣测……至于士孙瑞,”戏志才声音微沉,“此人表面恭顺,然其府中时有神秘客夜访,虽极力掩饰,然我辈亦能查知,访客多来自荆州、益州方向。彼等对天象之事,私下谓之‘甚为蹊跷’,然于公开场合,绝口不提。”
刘昆静静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王座扶手上轻轻敲击。这些老臣的反应,大多在他意料之中。天象的震撼,足以瓦解许多表面上的抵抗,但根深蒂固的忠汉观念与利益牵扯,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彻底清除。“此外,”戏志才补充道,“对于宫中陛下(刘辩)及一众内侍、宫人,皆已加派心腹,以护卫为名,严加监管。陛下自朝会后,愈寡言,每日除读书习字外,便是望天呆。董承等少数仍与之接触者,亦在其严密监视之下,暂无异常举动。百官之中,多数已认清时势,或主动靠拢,或静观其变,公然异议者,目下已近乎绝迹。”
刘昆微微颔,目光转向户部尚书黄玄:“黄尚书,朝廷府库,乃治国根基。东征淮南,耗粮几何?损饷几多?现今府库虚实,直言无妨。”
黄玄,一位面容精干、颧骨高耸的中年官员,应声出列。他手中捧着的是一本厚厚的账簿,脸上写满了忧虑。他深吸一口气,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回唐王,臣……臣正欲禀报此事。”他翻开账簿,语加快,“此次平淮南之战,历时半载,动用大军逾十万,民夫更众。虽沿途州郡供应、亦有缴获,然所耗钱粮,仍如流水!仅粮秣一项,便耗去太仓存粮近七成!军械打造、抚恤赏赐、牛马损耗……林林总总,折合五铢钱,恐不下三十万万!”
他抬头,脸上已无血色:“唐王,恕臣直言,如今朝廷库府,尤其是长安太仓、武库,几近空虚!各州郡虽有余粮,然转运艰难,且需备荒、维持地方。若再兴起一场如平定淮南般规模的大战,府库……府库绝难支撑!非但如此,去岁关中小旱,冀州蝗灾,皆需赈济。国库岁入,大半用于军资,余者维持朝廷运转已捉襟见肘。臣……臣恳请唐王,未来一两年内,若非不得已,务必休养生息,积累粮饷,否则,根基动摇,危如累卵啊!”言罢,黄玄深深躬身,几乎不敢抬头。
殿内一片寂静,只能听到烛火噼啪的轻微爆响。高顺浓眉紧锁,他深知广陵防务压力,若钱粮不济,何以对抗江东?其余众人亦面色凝重。国家机器的高运转,几乎耗尽了最后一丝元气。
刘昆的眉头终于蹙了起来。他预料到消耗巨大,却未想到已至如此窘境。他沉默片刻,缓缓道:“黄尚书所言,乃老臣谋国之言。大战之后,亟需休养,此乃常理。孤知道了。”他的目光继而转向一旁面色沉峻的御史大夫华歆:“子鱼,纠察百官,整肃吏治,乃你职责所在。如今朝野上下,风气如何?”
华歆闻言,立刻踏前一步。他面容端正,自带一股凛然之气,此刻却带着深深的忧愤:“唐王!臣正有本要奏!吏治之弊,触目惊心,贪腐之风,已非疥癣之疾,实乃心腹大患!”他声音陡然提高,带着痛心疾的味道:“自董卓乱政以来,纲纪废弛,法度不存。各地州牧郡守,拥兵自重,往往肆意征敛,中饱私囊。及至唐王定都长安,重整朝纲,此风虽稍有收敛,然诸多贪官污吏,更换门庭,巧立名目,其贪墨之本未改!如今朝廷财力困窘,与此辈蛀虫大肆侵吞,岂无干系?”
华歆从袖中取出一份奏疏,双手奉上:“臣近日查阅卷宗,暗中察访,仅司隶地区,去岁一年,涉及贪墨、盘剥百姓、克扣军饷之案,便有大小数十起!有县令强占民田,转手倒卖,获利巨万;有郡丞与豪商勾结,操纵粮价,大国难财;甚至……甚至军中,亦有军官虚报兵额,倒卖军粮马匹!各级官吏,相互包庇,已成网络。臣虽屡次弹劾,然往往阻力重重,或证据被毁,或人犯暴卒,或……或有更高层级者暗中回护!”他说到最后,语气已近乎愤怒,目光却下意识地快扫了一眼在场的同僚,似有所指。
“竟至如此地步?!”刘昆的声音陡然转冷,敲击扶手的手指蓦然停下。殿内温度仿佛瞬间降低了几分。他接过内侍传递上来的奏疏,并未立即翻开,而是目光锐利地盯住华歆:“都有谁?背后又是谁在回护?”
华歆深吸一口气,沉声道:“证据确凿者,名单在此。”他指了指奏疏后面附着的名单,“然其中牵涉甚广,不乏……不乏在座诸公之门生故吏,甚至宗亲。至于背后是否还有更深之黑手,臣……臣职权有限,恐难深究。”他话语中透着一丝无奈与不甘。
刘昆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他深知腐败对政权根基的侵蚀力,尤其是在这财力枯竭、亟需凝聚人心的时刻。黄玄汇报的国库空虚,与华歆揭露的吏治腐败,如同一体两面,揭示着庞大帝国肌体内部正在加溃烂的脓疮。“贪腐不绝,则国无宁日,民无生路!纵有雄兵百万,亦会被这些蛀虫从内部掏空!”刘昆的声音带着冰冷的杀意,“历朝历代,皆亡于吏治崩坏!孤岂能容此辈继续猖獗,毁我基业?!”
这时,礼部尚书刘岱出列附和:“唐王明鉴!吏治之弊,确需根除。然臣以为,堵截之余,亦需疏导。譬如,当重视官吏教化,更需重视其子弟教化。如今许多官员贪墨,除却自身贪欲,亦为聚敛财富以荫庇子孙。若能使官吏子弟皆有正途可走,有书可读,有才者可凭本事晋身,而非仅靠父辈财势,或可稍减其贪欲。故臣再次进言,请唐王加大力度,兴办官学,尤其面向军中将士及中低级官吏子弟,施以教化,导以正途。此乃长久之计。”
刘昆闻言,面色稍霁,颔道:“公山(刘岱字)所言有理。教化之本,不可轻忽。此事由你礼部牵头,会同相关衙门,详细拟定章程,尽快报与孤知。”他环视众人,最终目光落回华歆和一直沉默不语却面露激赏之色的刑部尚书卢植身上:“华歆、卢尚书。”
“臣在!”两人齐声应道。
“孤决定,即日起,在大汉治下所有州郡,展开一场彻底的反贪运动!由御史台牵头,刑部全力配合!华歆,孤予你全权,放手去做!无论涉及何人,无论其官居何职,背景如何,一经查实,严惩不贷!卢尚书,刑律方面,务必从严从快,以儆效尤!”
卢植立刻激动地大声道:“臣遵命!刑部上下,必竭尽全力,拥护唐王决策,肃清贪腐,还天下清明!”华歆亦是精神大振,深深一揖:“臣,领命!必不负唐王重托!”
刘昆沉吟片刻,又道:“然此事牵连必广,需讲究策略证据。对于朝中三品及以上大员,若有涉案,华歆,你不得自行处置,必须将确凿证据报于孤,由孤亲自定夺。三品以下官员,一经查实,你可先行抓捕、审讯,但所有案卷、证供,必须扎实,经得起推敲。若有无端构陷、屈打成招之冤案,”刘昆的目光骤然变得锐利无比,“孤唯你是问,并追究相关人等之罪责!”
“臣明白!定依法办事,以证据服人!”华歆凛然应诺。
会议又持续了近一个时辰,众人就反贪具体步骤、钱粮调度、军队整顿、教育兴学等事宜进行了详细讨论。刘昆虽雄心万丈,却深知积弊已深,不敢也无力一步到位,只能依托这些重臣,一步步稳扎稳打。
重臣会议结束后,已是黄昏。刘昆并未休息,而是屏退左右,只留下贴身护卫,悄然来到王府深处一间僻静的书房。书房内未有灯火,只有窗外残存的雪光映照,勉强勾勒出一个模糊的黑影,静立于房间角落,仿佛已与阴影融为一体。刘昆步入房内,对着那团黑影,淡淡开口:“出来吧。”
黑影闻声而动,悄无声息地滑至书房中央,单膝跪地:“臣,仇英,参见唐王。”声音沙哑低沉,仿佛刻意压制了原本的嗓音。此人全身笼罩极在宽大的黑色斗篷中,连面容都隐藏在深深的兜帽阴影之下,只露出一个线条冷硬的下巴。他,便是绣衣卫的第一任指挥极使,化名“仇英”的李儒。
“今日殿议,你都知道了?”刘昆问道,语气平静。
“臣已知悉。”仇英的声音里听不出丝毫情绪。
“孤欲彻查贪腐,然明面之上,御史台与极刑部,必有阻力,亦有光照不到之处。许多事,需要暗处的力量去做。”刘昆看着他,“绣衣卫初立不久,内部可还纯净?”
仇英微微抬头,兜帽下的阴影似乎波动了一下:“回唐王,绣衣卫吸纳人员复杂,确有前朝遗毒、各方眼线,甚至……亦有品行不端、欲借此权柄牟利之辈混杂其中。臣正欲请示唐王,进行内部整肃。”
“准。”刘昆毫不犹豫,“给你十天时间,将绣衣卫内部彻底梳理一遍。违法乱纪、心怀异志、能力不堪者,一律清除。必要之时,可用非常手段。孤要的是一把锋利且绝对听话的刀,而不是一把会伤及自身的锈刃。”
“遵命!”仇极英的声音里终于透出一丝难以抑制的兴奋,那是一种得到授权、可以放手施展的黑暗快意。
“整顿之后,绣衣卫要任务,便是配合、协助华歆的反贪行动。你们负责暗查、密捕、审讯,为御史台提供他们难以获得的铁证。孤授你权柄,可查任何品级官员。记住,三品以上,证据报孤;三品以下,你可自行决断,但证据必须确凿,若制造冤狱,孤便用你的头来平息众怒。”
“臣明白!定不会让唐王失望!”仇英的声音因激动而愈沙哑,“臣以性命担保,绣衣卫所出每一份证供,皆乃铁证!”
“去吧。”刘昆挥挥手。仇英再次无声叩,身形如鬼魅般退入阴影,悄然离去。
化名黄重(原董璜)的绣衣卫副指挥使很快被仇英召见。在绣衣卫阴森隐秘的总部内,烛光摇曳,映照着仇英兜帽下冰冷的嘴角和黄重略显惶恐又带着几分狠厉的脸。“唐王有极令,绣衣卫即刻起,内部整顿,清除败类!随后,全力投入反贪风暴!”仇英的声音不容置疑,“黄指挥使,你负责甄别内部所有人员,凡有疑点者,先行控制。十日内,我要看到一个干净的绣衣卫!”黄重心中一凛,连忙应下。他深知这位神秘上司的手段。
紧接着,一份份密令从绣衣卫总部出,一张无形而严密的大网悄然撒向长安乃至各州郡的官场。熹平八年正月,本该是喜庆祥和的氛围,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席卷整个大汉治下的反贪风暴彻底打破。
![[综英美]在哥谭捡超英代餐](/img/43717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