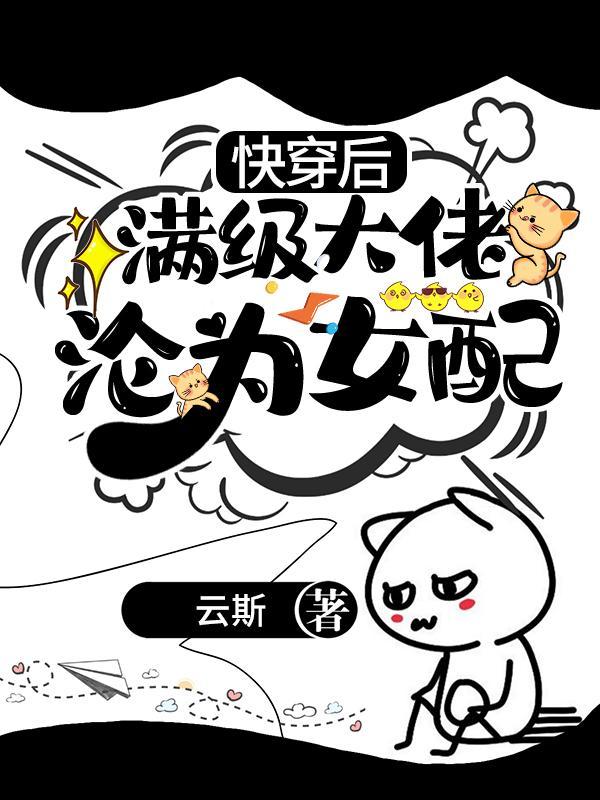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手搓弓弩养娇妻,竟要我黄袍加身 > 第274章 日进斗金(第2页)
第274章 日进斗金(第2页)
“太子与十四皇子,因豫州水患赈灾粮款的去向,在朝堂上已近乎撕破脸皮。太子指责十四皇子督办不力,致使粮款被地方官吏层层盘剥;十四皇子则反咬太子门人插手赈灾,中饱私囊。”
“右相柳越,表面和稀泥,实则暗中授意门下御史,连上三道弹劾十四皇子‘督抚不力,有负圣恩’的奏章。”
“看来,柳相更加偏向太子了。”陈锋心中暗道。
她又拿起第二本《军务卷》,递给关无情:“关统领,这是你那边汇总的。”
关无情接过,翻开:“淮水截杀案,那批神臂弩的源头,指向京郊兵部直属的‘甲字三号’武备司。该司郎中,张德禄,是太子妃远房表亲,太子府詹事张之谦的侄子。线索到此中断,但矛头已指向东宫。”
他顿了顿,补充道:“另,镇北侯府夜袭案,与淮水非同一批人。府中刺客所用兵器虽寻常,但配合默契,进退有据,绝非寻常江湖草莽。其目标明确,直指公子,不似柳越手笔,反与主战派内部某些急于排除异己的激进作风吻合。”
陈锋眉头微蹙:“主战派内部?我自问从未得罪过军中同袍,反而一直在为边军筹谋。”
“公子可还记得冀州刺史严桧?”关无情抬眼,“那块求贤令,是柳越授意严桧所。在有些人看来,公子您接了柳越的令,便是与柳越有了牵扯。主战派内部,并非铁板一块,有人恐公子日后成为柳越打入军中的一枚钉子,故而……欲除之而后快。”
陈锋眼中闪过一丝寒芒。原来如此!竟是这般可笑的猜忌!
谢云娘拿起第三本《世家卷》,只略翻了翻,便放下,最后拿起那本陈锋最为关注的《科场卷》。
“会试在即,此次会试主考官,国子监祭酒郑玄,已入贡院‘锁院’。”谢云娘的声音带着一丝凝重,“此人,素有‘铁面’之称,为人古板方正,治学严谨,尤重经义基础,文章风格要求四平八稳,最厌恶华丽辞藻与离经叛道之言。坊间传闻,其判卷标准,近乎苛刻。”
她翻到册子中间一页,上面用蝇头小楷记录着不同客人酒后吐露的只言片语,拼凑出一个立体的郑玄。
“郑玄出身寒微,全赖寡母含辛茹苦抚养成人。其母李氏,如今已年过八旬,双目失明,卧病在床。郑玄此人,官声清廉,不近人情,唯有一‘孝’字,可称至诚。每日下朝,无论多晚,必亲至母亲榻前侍奉汤药,寒暑不辍。其母一言,于他而言,重逾千金。”
她合上册子,看向陈锋:“最关键的是,柳越的几个得意门生,如范阳卢氏的卢子瑜、河东薛氏的薛文瀚,此次也是北闱的夺魁热门。”
“昨日,有客人在‘翰林’雅间醉酒后失言,提及柳越似乎通过某种隐秘渠道,提前得知了郑玄此番策论可能侧重考察的几个方向,已命其门生据此闭门猛攻,押题准备。”
“押题?”陈锋冷笑一声。
他看着手中的情报,在书房内来回踱步,陷入了沉思。
敌人已经提前知道了“考纲”,这对于科举而言,是致命的优势。自己若还是按部就班地去温习那些四书五经,即便文章写得再好,也未必能胜过那些有备而来的对手。
必须另辟蹊径!
科举,从来不只是才学的较量,更是信息的博弈,人心的揣度。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划过石案冰冷的表面,最终停留在《科场卷》中关于郑玄“至孝”的那段描述上。
对付郑玄这种“又臭又硬”的石头,光有惊世之才是不够的,必须“投其所好”,撬动他心中唯一柔软的那块地方。
一个大胆而精妙的计划,如同黑暗中擦亮的火花,瞬间照亮了他的脑海。
他要做的,不仅仅是写出一篇让所有人都赞叹的好文章,更是要写出一篇让郑玄这位“铁面御史”无法拒绝、甚至会拍案叫绝的文章!
陈锋将那份关于郑玄的情报,从卷宗中单独抽了出来。
他的手指,在“孝”那个字上,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嘴角,浮现出一丝莫测的笑容。
“柳相,郑大人,这次的会试,恐怕要让你们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