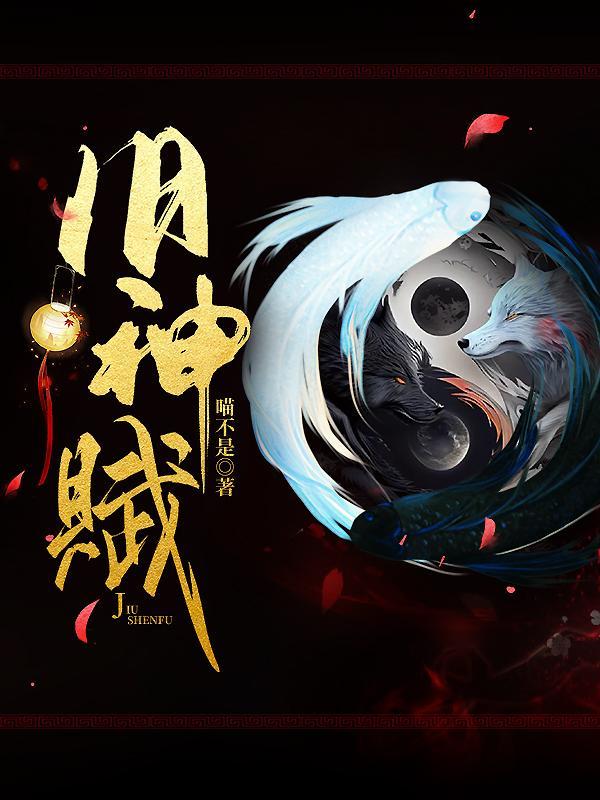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手搓弓弩养娇妻,竟要我黄袍加身 > 第265章 谋锦绣(第1页)
第265章 谋锦绣(第1页)
当夜,陈锋回到镇北侯府,将今日与吴万里交涉的情况详细告知了林月颜和叶承。
林月颜听完,眉头微蹙:“金陵商会如此霸道,竟敢明目张胆地阻挠,这……”
叶承在一旁气得直拍桌子:“太过分了!大哥,要不咱们亲自上门找他谈谈,有镇北侯府出面,看谁还敢刁难!”
陈锋摇头:“不可。我们是要做风雅之事,若动用武力,反而落了下乘。况且,金陵商会背后,恐怕也牵连着不少朝中大员,镇北侯府若出面,反而会打草惊蛇。”
林月颜点头:“夫君说得是。若动用武力,反而显得我们底气不足。”
她沉吟片刻:“夫君,我记得谢夫人之前说过,金陵商会会长郝万金,与柳越大人关系密切。此人惯会钻营,手段毒辣,人称‘郝黑手’。”
陈锋眼睛点头:“不错。看来,我们得换个思路。”
他站起身,走到书房的舆图前,手指轻轻点在秦淮河畔:“吴万里不过是个卒子,背后站着的是整个金陵商会。若想拿下‘锦绣阁’,就得先破了这商会的阵脚。”
叶承挠头:“可咱们怎么破?商会那帮人,抱成一团,铜墙铁壁似的。”
林月颜轻声道:“夫君,谢夫人是商场老手,她定有对策。不如明日再去见她,商议对策。”
陈锋点头:“正是此意。”
……
次日清晨,陈锋来到谢云娘租赁的临时府邸。
书房内,谢云娘亲自为陈锋沏了一壶上好的大红袍,凤眸中不见了昨日的恼怒,取而代之的是商人的冷静与锐利。
“陈公子,看来我们都小瞧了金陵商会的凝聚力,或者说,是小瞧了他们排外的决心。吴万里那只老狐狸,不过是仗着背后有人撑腰。我已派人打听了一下,金陵商会会长郝万金亲自了话,谁敢把核心地段的铺子卖给我们谢家,就是跟整个商会为敌。”
她顿了顿,继续道:“我试着动用了些在官府的关系,想从房契地契的文书审批上给吴万里施加些压力,结果也是石沉大海。那些官吏,要么是拿了商会的好处,要么就是不愿得罪这群地头蛇,都在和稀泥。这条路,怕是也走不通。”
陈锋品了一口茶,茶汤醇厚,回味甘甜。
他不急不躁地说道:“意料之中。蛇有蛇路,鼠有鼠道。既然明路走不通,那我们就……走暗道。对付这种滚刀肉,跟他讲道理、拼财力是没用的,必须找到他的痛处,狠狠地打下去,打到他皮开肉绽,跪地求饶为止。”
谢云娘眼中精光一闪,身体微微前倾:“哦?听陈公子此言,竟是早已料到此局,心中已有破局之策?”
陈锋放下茶杯,看着她:“我负责出主意,找人。但在此之前,我需要一样东西——情报。关于那个吴万里,越详细越好。他的家世背景、人脉关系、生意状况,尤其是……他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癖好、或者把柄。此事,是夫人的强项。”
谢云娘笑了,笑得像一只成竹在胸的狐狸,风情万种:“公子放心。论及打探消息、收集情报,我谢家经营数百年,若自称第二,这金陵城内,怕是没人敢认第一。”
“给我三天时间,我保证把吴万里从小到大穿什么颜色的亵裤,都给你查得一清二楚。”
……
三日时光,转瞬即逝。
第四日上午,陈锋再次来到谢云娘的书房。
谢云娘早已等候多时,她面前的书案上,摆放着厚厚一沓装订整齐的卷宗。
见陈锋进来,她也不多寒暄,直接将卷宗推到他面前。
“公子请看。”谢云娘指着卷宗,条理清晰地介绍道,“吴万里,金陵本地人,祖上三代都是小商人。他本人并无多少经商才能,全靠着祖产和金陵商会的庇护,才勉强维持。‘锦绣阁’的生意,早已是连年亏损,全靠拆东墙补西墙在硬撑。他表面风光,实则内里早已被掏空。”
她熟练地翻过几页,指着其中一行记录,语气肯定地说道:“而他最大的命门,在这里——此人极好赌博,且赌瘾极大,又毫无自制力。金陵城内大小赌场,几乎没有他不去的。尤其嗜好去城南一个由黑道头目‘豹爷’掌控的地下赌场‘通天坊’。那里赌得大,输赢也狠。”
她又翻开另一页,上面密密麻麻抄录着许多数字:“这是我们的人,花了不小的代价,从‘通天坊’一个管账先生那里弄来的账目抄录。清晰记载着,吴万里在‘通天坊’前后累计欠下了高达五万两白银的巨额赌债,皆是利滚利的高利贷。”
“按照豹爷那儿的规矩,这笔债拖到今日,利滚利,没有七万两绝对无法平账。那豹爷此前大约是顾忌他金陵商会成员的身份,又或是想放长线钓大鱼,一直未曾真正下死手逼债。但这笔债,就像悬在他头顶的一把刀,随时都可能落下来。”
陈锋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卷宗上不仅有吴万里的赌债记录,甚至还有他偷偷养在外面的外室、以及他儿子不成器,在书院屡屡惹是生非的劣迹,情报之详尽,令人咋舌。
看着这些赌坊的资料,他不禁想起自己穿越来之前的经历。那时的他,不过是清河村一个游手好闲的混混,在王大疤瘌的赌坊欠下不少钱,差点就把妻子林月颜卖了抵债。好在自己穿越而来,才避免了那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