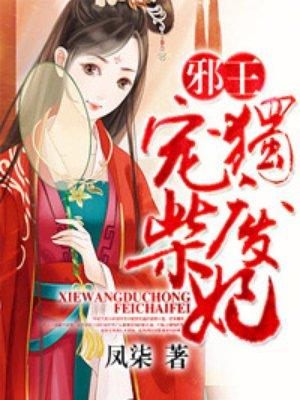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算鼎三国:玄镜红颜录 > 第865章 雍凉蓝图经略天下(第2页)
第865章 雍凉蓝图经略天下(第2页)
待亲兵将两盏滚烫的、茶汤浓酽的陶碗分别置于我们面前的矮几上,氤氲热气升腾而起,模糊了彼此部分面容时,我才重新坐回主位。
我没有迂回寒暄,直视着热气后那双依旧挣扎的眼睛,开门见山,语气坦诚:
“义山公甘冒奇险,深夜轻身来此,心中必有万千权衡,最终择此一路。昭感其诚。在公做出任何决断之前,想必胸中块垒犹在,疑虑未消。此处别无六耳,公有何言,尽可直言相告,昭必倾心以对。”
杨阜没有去碰那盏烫手的茶,只是任由热气扑在脸上,仿佛那点暖意能稍稍驱散他内心的冰寒。
他沉默着,帐内只闻炭火偶尔的噼啪与壶中水将沸未沸的细响。这沉默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长到足以让任何等待者心焦,但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等待着。
终于,他像是耗尽了所有支撑的力气,肩膀几不可察地塌下去一丝,缓缓抬起头。
他没有看我,目光空洞地落在跳跃的烛火上,声音沙哑得如同粗糙的砂纸相互摩擦,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肺腑深处艰难地挤出,带着血沫的气息:
“陆使君……今日阵前,阜……已是心神俱溃,体无完肤了。”
他顿了顿,深吸一口气,那气息颤抖着:
“阜,幼读诗书,长习经义,自负知晓忠孝节义为何物。一生所为,自问皆求无愧于心,无愧于凉州乡梓。守冀城,抗……抗将军麾下雄师,亦自以为是在守土卫道,存续汉家一缕正气于边陲。”
他的语气渐转沉痛,充满了自我拷问的煎熬:
“然……然使君一席话,如惊雷贯耳,白日施粥之举,更似烈火灼心。回头再看,阜之所谓‘忠’,是忠于一姓之刘,还是忠于天下万民?”
“阜之所谓‘义’,是囿于一方之土、一门之私的狭隘之义,还是放眼九州、使生灵免于涂炭的大仁大义?守此孤城,外不能御羌胡,内不能安黎庶,徒令城中百姓饥馑,城外士卒殒命……这‘忠义’二字,何其苍白,何其……虚伪!”
他的声音陡然拔高,又迅低落下去,化为无尽的自嘲与痛苦,
“到头来,阜不过是一叶障目、助长战祸、徒令生灵遭劫的糊涂虫罢了……读了一辈子圣贤书,竟读成了个冥顽不灵的蠢物!”
说到此处,他猛地抬起手,捂住了脸,肩膀剧烈地耸动起来,不是哭泣,而是一种情绪剧烈冲刷下的难以自持。
良久,他才放下手,眼眶通红,却已无泪,只剩下一种近乎虚无的平静,但那平静之下,是信仰崩塌后的废墟。
“阜,败了。”
他直视向我,这一次,目光里没有了白日里的敌意与激愤,只有一片荒芜的坦然,
“非但败于使君军势之强,谋略之高,更败于使君所持之理,所行之事。阜……心服,口服。”
然而,就在这似乎一切尘埃落定的认败之语后,他眼中那原本黯淡的光,却骤然重新凝聚起来,变得锐利如锥,仿佛回光返照般,迸出最后的力量,死死地盯住我,那目光似乎要穿透我的血肉,直窥灵魂最深处:
“但,陆使君,阜败则败矣,心中仍有一问,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他的身体前倾,双手撑在膝上,指节因用力而白,每一个字都咬得极重:
“就算如使君所言,曹孟德是国贼,挟天子而令诸侯,其心可诛!就算使君你,军纪严明,善待俘虏,今日更施粥于饥民,堪称仁义之师!”
“可这雍凉之地!”
他手臂猛地一挥,指向帐外无尽的黑暗,仿佛能看见那片广袤而苦难的土地,
“自桓灵以来,便天灾不断,羌胡屡叛!董卓之后,更是战乱频仍,李傕、郭汜、韩遂、马腾……你方唱罢我登场,无岁不战,无地不残!十室九空,白骨蔽野,易子而食之事,绝非古籍传闻!”
“羌、氐、匈奴诸部,趁隙侵扰,边民朝不保夕!此地早已是元气大伤,满目疮痍,民力枯竭到了极致!”
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再次颤抖,却充满了最后的、近乎绝望的质疑:
“你陆昭,今日能得冀城,明日或可得陇西,得整个凉州!可你得了这片土地之后,又能如何?!”
“你凭什么,让这片土地上苟延残喘的百姓相信,你带来的,不是又一轮的征伐、压榨与战乱?”
“你凭什么,能给他们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军阀、任何豪强的、真正可以期待的、太平安稳的未来?!”
“若你不能,那你今日之‘仁义’,与往日那些打着各种旗号、最终却将凉州拖入更深苦难的枭雄,又有何本质区别?!”
“这难道不是又一个循环的开始吗?!”
这个问题问得极其尖锐!
也问到了所有雍凉士人心中最深的那个症结所在!
他们不怕死。
他们怕的是永无休止的折腾!
是换了一个主子,却迎来更加悲惨的命运!
我没有立刻回答。
我站起身,走到了帅帐中央那副巨大的雍凉地图之前。
帐内的烛火,将我的身影投射在地图之上,仿佛要将整个雍凉都笼罩其中。
“义山公,问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