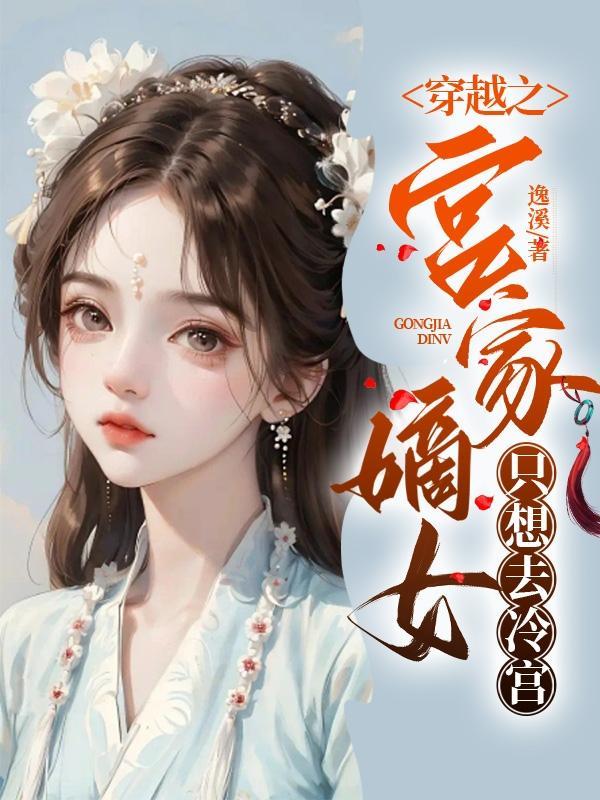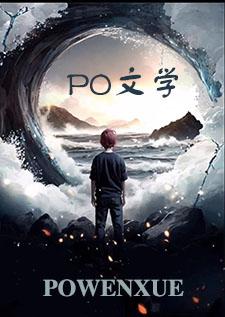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算鼎三国:玄镜红颜录 > 第665章 庶务千头徐公运筹(第1页)
第665章 庶务千头徐公运筹(第1页)
夺取南郑,雷霆震慑,政令连,激浊扬清。
看似大刀阔斧,势如破竹。
然而,真正的考验,从来不在于口号喊得多响亮,政令颁得多严厉,
而在于如何将这宏伟的蓝图,一丝不苟地落实到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具体的环节之中。
这几日,我将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军队的整肃和城防的巩固上,确保手中最坚实的“枪杆子”牢牢握紧。
而新政推行的繁杂庶务,则几乎全权交由了徐庶,徐元直。
太守府后院临时开辟出来的几间厢房,如今已成了整个汉中新政权最繁忙的中枢。
这里没有雕梁画栋,没有繁文缛节,
只有行色匆匆的吏员,堆积如山的简牍文书,
以及弥漫在空气中那股混杂着墨香、汗水和某种难以言喻的“新生”气息。
我踏入这片区域时,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景象。
几张简陋的木案拼凑在一起,便是临时的“户曹”所在。
几名穿着洗得白的旧吏袍,但眼神却异常明亮的年轻人,
正埋于一堆绘制粗糙的地图和登记册中,激烈地争论着什么。
他们的手指在图上划来划去,时而皱眉,时而比划,显然是在为田亩清丈的具体方法而绞尽脑汁。
隔壁的“兵曹”雏形处,则围着几名军中提拔起来的识字都伯、什长,
他们正对着一份份歪歪扭扭的功劳簿,核对着夺城之战中士兵们的具体战功,
旁边有人用炭笔在木板上记录,不时为某个名字的归属或功劳大小争得面红耳赤。
这关系到他们能否获得土地,能否改变命运,由不得他们不较真。
再往里走,一间稍大些的屋子被辟为“工曹”和“仓曹”的联合办公地。
角落里堆放着一些矿石样本和初步铸造出来的“汉中五铢”样币,
几名老匠人模样的男子正对着炉火和模具比比划划。
而另一侧,则是糜信派来的几位精干的账房先生,
正在清点从张鲁府库中接收过来的粮秣物资,算盘珠子拨得噼啪作响,每一笔都记录得清清楚楚。
而统筹这一切,让这看似混乱却又充满活力的机器得以运转的核心人物,便是徐庶。
我找到他时,他正站在一幅巨大的汉中舆图前,眉头微蹙,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他的眼圈有些黑,下巴上也冒出了青色的胡茬,显然是几日未曾好好休息。
但他挺拔的身姿依旧如松,眼神清亮,丝毫不见疲态,反而透着一种运筹帷幄的沉稳和专注。
听到我的脚步声,他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一丝歉意的微笑:
“主公来了。庶务繁杂,未能远迎,还望恕罪。”
“元直辛苦了。”
我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礼,
“我只是来看看,新政推行,千头万绪,你这边可还应付得来?”
“千头万绪,确是如此。”
徐庶坦然承认,指了指周围忙碌的景象,
“主公的三大新政,环环相扣,皆是革故鼎新之举,牵一而动全身。
要将其真正落到实处,绝非易事。”
他走到“户曹”那边,拿起一份刚刚绘制出的田亩清丈草图,对我说道:
“就以这‘军功授田’为例。
想法虽好,但要实行,要便是清丈田亩,核实人口。
汉中地形复杂,山川纵横,张鲁治下多年,
田亩册籍本就混乱不清,更有大族豪强隐匿田产、人口,层层阻碍。
我们人手不足,缺乏经验,要将这笔糊涂账彻底理清,难如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