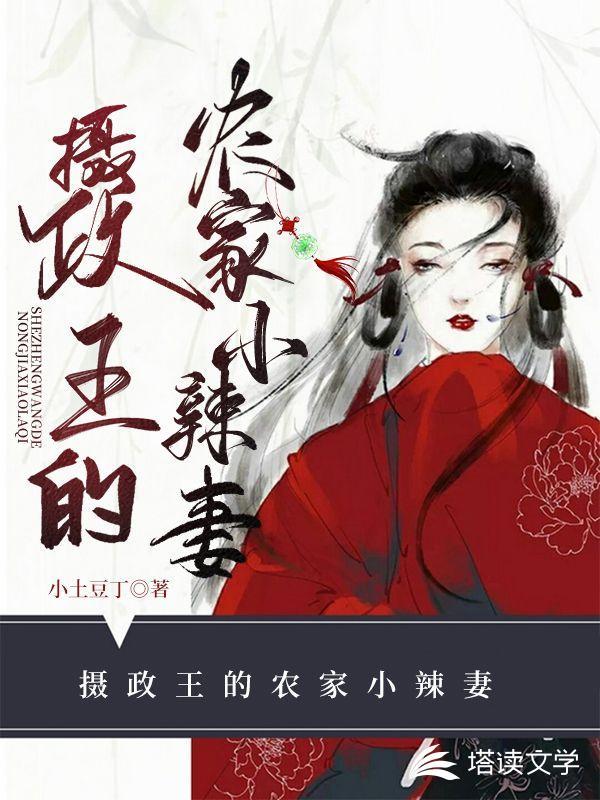九五小说网>雪中孤城:疫病封锁下的末日求生 > 第246章 荒野求生(第3页)
第246章 荒野求生(第3页)
这玩意儿结实,等会儿捆柴正好派上用场。
心里盘算着回去的事:得在洞里凿个小凹槽当火塘,不能太大,不然热量散得快。
还得从凹槽顶上往上挖个透气孔,斜着通到外面,得够细,既能排烟又别灌太多风。
不然木头烧起来,废气排不出去,不等冻僵先得被熏死。
到了倒树旁,张涵的手像有自己想法似的,摸进怀里掏出那包皱巴巴的水果糖。
包装纸冻得脆,手指僵得打不了弯,撕了两下才扯开个小口,糖粒在里面滚了滚。
往嘴里塞了两颗,西瓜味混着草莓味在舌尖炸开,甜得有点齁,这点热量顶不上什么用,却勾得他喉咙紧,真想把整包都倒进去。
甜能让人忘了冷,忘了累,就这会儿的功夫,连胳膊的酸都轻了点。
他抬手往脸上扇了一巴掌,“啪”的一声脆响混在风里。
“省着点。”他对自己嘟囔,唾沫星子刚出口就成了白汽。
把剩下的糖纸裹成个小团,塞回怀里贴胸口的地方,保暖底下还有点体温,能让糖粒别冻成冰疙瘩。
要取暖,木头得够分量。
细枝子烧起来“噼啪”响,看着热闹,其实一袋烟的功夫就化成灰了。
可那松树主干粗得像水桶,冻在地里跟长了根似的,凭他这胳膊腿,想劈开纯属瞎琢磨。
只能挑那些碗口粗的侧枝下手。工兵铲的钝边往冻硬的木头上砸,“咚、咚”两声,天太冷,木头早冻透了,纤维脆得像屋檐下挂了一冬的干柴,看着硬邦邦,实则不经砸。
第三下他憋足劲抡下去,“咔嚓”一声脆响,枝干断成两截,断面的木茬带着冰碴溅起来,打在脸上有点凉,有点疼。
就这么一下下抡着铲子,胳膊酸得像坠了块石头,抬起来都得咬着牙。
每劈断一根,就抬脚往旁边踢踢,归成一小堆,雪被踩得“咯吱”响,鞋底子早冻硬了,感觉不到冷,只觉得沉。
没多会儿劈够了两捆,每一捆七八根,长短截得差不多,黑黢黢堆在那儿,看着够烧小半夜。
张涵跪在雪地里,膝盖陷进半尺深,雪的凉气顺着裤腿往上钻,膝盖麻得快没知觉了。
把步枪背带解下来铺开,柴捆往背带中间拢,系结时试了三次才打成死结,使劲拽了拽,结头勒进木头缝里,纹丝不动,结实。
可抓着背带往肩上扛时,才知道这分量有多沉。
刚把柴捆提离地面,脚下的雪就“噗”地陷下去,没到大腿根,雪灌进裤管,凉得腿肚子一抽。
想直起身,膝盖在雪里晃了晃,站不稳,柴捆坠得肩膀紧,像勒了道铁圈,脚下的雪还在慢慢往下塌,带着他往一边歪。
“操。”张涵低骂一声,知道站着走不成。
松开一只手撑在雪地上,掌心按进雪里,把柴捆往背后挪了挪,整个人趴在雪上,胸口贴着雪面。
就这么一点点往前爬,膝盖和手肘在雪里蹭出两道沟,雪沫子顺着袖口、领口往里钻。
柴捆在身后拖着,枝桠刮过雪地出“沙沙”声,每挪一下,都能感觉到雪在身下缓慢下陷,但比站着时稳多了。
至少不会一下子陷到大腿根。
头顶的枯叶间漏下几缕灰蒙蒙的光,雪片在光里打着旋飞,像无数细小的白虫子。
张涵忽然想起某期节目里,主持人说“生存的关键不是多复杂的技巧,是把最简单的事做对”。
现在趴在雪地里,他信了。
没本事搞那些复杂的,没力气挖更深的洞,更没有结实的身板,就只能凭着这点零碎记忆,劈柴,捆柴,哪怕是像这样爬着往回挪。
把眼下能做的做好,就够了。